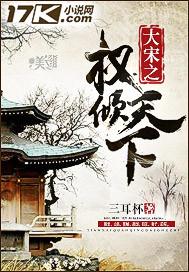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小白花lyx > 客栈逸事(第1页)
客栈逸事(第1页)
邱海棠还未及笄,谈婚论嫁对她来说言之过早,但她也知道嫁衣是女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服饰之一。
民间嫁新娘的传统繁复,上至盖头、发钗,下至腰饰、绣花鞋,处处都有讲究,须得一身红艳艳、金灿灿的,越喜气越金贵才好。
一时半刻她还真想不出什么稀罕的图样,可不能怠慢了叫人空欢喜一场,要是娘亲从前出嫁的那身行头还在,就能找出来让她参摹参摹,可惜那场大火烧得一穷二白,就算侥幸没有大火,邱二伯也会拿去换钱,恐怕一根金线也不会给她留。
邱海棠兜着收拾好的包袱往回走,她这次出来本想将二伯母寄来的首饰当了,看看能不能凑个整,但这些当铺实在黑心,还不如留着以后给邱岁聿做个念想。
她知道冯粟家是跟货船做生意的,跑一趟船就顶寻常人家干好几年,倘若她能将冯粟出嫁的盖头设计好,兴许能多得些赏钱。
这么一想她心中总算有了些慰藉,步子也松快许多。
谁承想高兴的这股劲还没喘过一口气,不知道打哪掉下来一颗咬了一半的果子,在她衣服上砸了个小黑点。
邱海棠现在落魄得本就没几件像样的好衣服,这飞来横果让她直接怒气飙升。
“谁啊,不晓得嘴上积德!”
话音刚落,同一个方向又砸下来一颗,这次是个圆整的。
邱海棠捂着头险险躲过,气得眼睛冒火,后退了好几步抬头往上望,和头上绑了个绿丝巾的邱二伯面面相觑。
“我。。。。。。”
真是瞌睡了送枕头说什么来什么,邱海棠把包袱往背上一甩,撸起袖子就往正对着的客栈里冲。
店小二招呼不及:“客官几位?住店还是打尖?”
“找人!”
邱二伯丢果核的位置十分好找,正对着一扇二面开的窗户,邱海棠杀上去的时候那货四下躲藏无门,正一脚跨坐在窗沿边,作势要跳下去。
邱海棠晓得他贪生怕死,倒是把后头跟着的店小二吓个半死。
“哎呦,客官你这是做什么!快下来!”
邱海棠将包袱顺手撂在桌子上,心不慌手不抖,眼瞅见桌上三菜一汤还添了壶酒,看来自赌场一别后她二伯这小日子依旧优哉的很。
酒壶旁边还送了盘果脯,颜色乌黑看不出是什么,和她衣服上那漆黑的一点污垢倒是对上了。
邱海棠抓起一把在手里,手中做投掷的动作,一颗一颗往邱二伯身上招呼。
邱二伯只能拼命躲闪,捂着脑袋坐在窗沿上好生狼狈。
“死丫头片子!你就是这么对长辈的?”
邱海棠手上动作更快了,一把砸完索性直接端着盘子往他脸上泼,嘴上也毫不留情:“你算哪门子长辈,出了事卷钱跑路,亲儿子的命都不要了!”
店小二夹在他俩中间左右为难,弱弱的一句“你们不要再打啦”还没说完就被陡然拔高的争吵声淹没。
邱二伯一边躲一边挥舞着手臂企图反击,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先前在赌坊坑邱海棠替他还了四十两,他竟不同往日那般泼皮无赖,甚至有点心虚。
邱二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带着邱岁聿住进秀才家了,他家好啊,手头富裕又没孩子,你们是不是想改姓陆啊!”
邱海棠心里咯噔一下,手上的动作停滞:“你胡说什么!你知不知道邱岁聿他腿不行了,现在下地走路都困难,他姓邱,但你管过他吗?”
邱二伯不甘示弱,怒气上头口不择言道:“他是姓邱,但是不是老子的种还不一定呢!”
邱海棠惊骇,回神后不管不顾地冲过去揪着他的衣领将人往下推。
邱二伯一时不防,重心不稳,摇晃几下后牢牢地扒住窗户框,一只脚拼死往地上够,嘴里咋咋呼呼地喊:“杀人啦!还有没有王法了!”
店小二怕闹出人命,快步上前将邱二伯拽了下来。
结果邱二伯死性不改,前脚刚稳稳落地,下一秒就伸手将邱海棠往窗口推。
那窗户大开,邱海棠身形又小,若非前头有张凳子绊了一跤,真要整个人翻下去。
邱二伯行事虽无端,但也没真胆大到敢杀人,刚刚那一举动完全是被愤恨冲昏了头脑,现在反应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快跑。
但不等他爬起来,邱海棠抱起一旁的凳子压在他身上,将人牢牢桎梏在原地。
邱二伯只能像泥鳅一样在地上一个劲地乱窜,配合他头上摇摇欲坠的绿丝巾,相当滑稽。
“你刚刚那话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