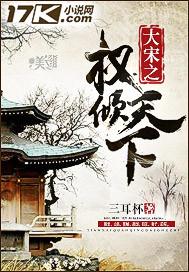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天龙八部肖峰主演 > 第118章(第1页)
第118章(第1页)
阿碧伸出纤手接过。油布包儿里躺着一枚御印火漆封的手谕,另有一面一尺长的朱漆木牌,上篆八个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她低头瞧了一会儿这两样物事,眼中光彩逐渐黯淡,叹道:“公子爷拢家才勿到两天辰光,今儿个短短一歇,已经来了四五拨人哉,都是送介格牌子。官家啥事体?找我公子爷介么十万火急?……他身子还勿曾大好呢。哪能伤也弗准人养了么?”
军官见了她愁苦模样,不由心一软,柔声道:“御前文字,事涉军机,俺无缘看得,但想必跟近来宋辽边境异动大有关系,这才要火急火燎起用你家将军。慕容将军威震东西,敌人闻风丧胆,此事多半还得要他出来主持局面。男儿志在边关,小娘子勿要伤心。官家手谕,就拜托娘子代为转交。”
阿碧默然片刻,随即振作精神,微笑道:“是。……军爷弗喝口水再去么?”
军官摇头道:“俺要回京覆命,不敢多留。”说着一揖,牵马认镫,翻身上了马背,匆匆地正要去,忽似想起一事,拨转马头,向着阿碧扬声道:“娘子,今天过些时候只怕还有金牌飞马送到。后面还跟着多少俺却说不好。劳累你安排一个家里人在这湖边候着罢。”说着径直匆匆去了。
阿碧瞧了一会儿他飞驰远去的背影,慢慢将油布包儿收入怀中,背过身去,悄然抬手拭了拭眼角,叹一口气,提起长篙,于岸边轻轻一点,“吱呀”一声,一叶轻舟无声无息地滑入湖心,搅碎了满湖天光云影。
※※※
“……东北龙城,龙兴之地,老爷假死二十年,却也没闲着:他于此处招兵买马,颇招揽了一批能人异士,又积攒了一批军火弓箭,粮草金银,均藏于慕容家地宫之中,这张藏宝图便是凭据。倘若以此地为基本,扯一支义旗,届时公子爷带大兵至雁门关时,天高皇帝远,起兵与它遥相呼应,复国哪里是甚么难事!”说话的是公孙乾。他于一面展开的地图前来回踱步,时不时伸手指点,挥斥方遒,眼睛激动得闪闪发光,面色微红,似乎已然看见了慕容复黄袍加身的情景。
“非也非也。”包不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抬手以指关节敲击地图上龙城,声色俱厉地道:“公孙二哥算岔了。龙城虽是慕容氏龙兴故都,却并非起兵的所在。你瞧龙城与辽国燕云十六州之间,只隔一线天堑,难守而易攻。届时倘若辽国弃守雁门关,转头以全力攻打,龙城哪里守得住?依我之见,还是先取契丹:耶律洪基此时全力南下,国中兵力必然空虚。倘若我此时调动辽北汉儿山寨奇兵,出其不意,先取它上京,再乘士气旺盛,一鼓作气攻破其余四京,辽国版图在握,何惧什么大宋,什么西夏!”
“你那山寨义军才区区二万人力量,上京却是雄关如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如何攻得破上京!”公孙乾伸手于桌上重重一拍,将空茶碗、残烛、果皮带得一并跳了起来,高声道。
邓百川最为冷静持重,这时站出来将手一摆,出言劝阻:“大家有话好说。二位兄弟切莫伤了和气。”
“都争了一日一夜了,也争不出来个结果。大哥,你却是什么主意?”不意公孙乾扭头将他一军。
邓百川思忖片刻,字斟句酌,沉思地道:“……依做哥哥的瞧,现在……只怕还不到大举兴兵的时候。”他这番话说得甚是吃力,但言辞恳切。“公子爷如今尚未大好。我不想令他带兵涉险……”
他话音未落,门扇上忽起了两声剥啄。屋内众人尽皆一惊,一直坐在角落未曾出声的风波恶跳起身来,厉声喝道:“谁!”话音未落,闪身已到了门前,一把将门拉开。
门口站的却是阿碧,纤弱弱、怯生生,柔声唤了句“四哥”,将一只油布包儿双手递了上来。
风波恶一愣,脸色一缓,柔声道:“阿碧小妹子,是我不好,吓着你啦。”说着接过布包,打开看了一眼,脸色登时一沉,一语不发地捧着快步走至慕容复面前,唤了一声“公子爷”。
慕容复坐直身。他眼下有轻微的青印,显见也跟邓百川几人一样,一天一夜未曾合眼。他并不接过,只心不在焉地于风波恶手中扫了一眼金牌手谕,简短地命令道:“念。”
风波恶拆信才念了两句,被他一扬手止住,道:“不必再念了。”手谕上果然还是那一套‘见朕手谕,火速归京,公忠体国,为国前驱’的老话。
他神色疲惫,以手支额,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自风波恶手中接过那面传令金牌,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两眼,无声地笑了一笑,顺手往桌上一丢,立起身来。
“公子爷是什么主意……?”邓百川小心翼翼地问。
慕容复恍若不闻,拉紧肩头鹤氅,径直缓步朝门口走去,头也不回,亦不发一语。邓百川、包不同几个面面相觑,这互一望间,慕容复已经走远。
暮色四合。
慕容复脚步不疾不徐,衣袂随着步伐翻飞。出得书房,于山石花木间东一绕,西一跨,穿过重重房舍院落。
柳暗花明,山穷水尽,眼前陡然开朗,一道长长的青石阶依山蜿蜒没入林子深处。他毫不停留,缓步拾级而上。山路险峻,林木间掩着一座清净别院,并无牌匾。
上得山来,慕容复并不进院,径直向后山走去。
后山一片树林,尽皆生长着参天古木,清幽庄严。林中一座清净庙宇,两旁散植果木,枝头开着星星点点的白花,香气暗暗浮动。庙旁空地上坟起一座土丘,丘上坐着个花白胡须的中年男子,头戴高高的纸冠,神色俨然,口中念念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