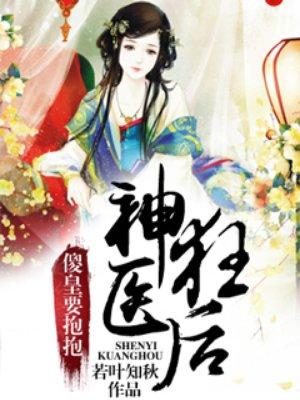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复原反应abo攻和谁在一起了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林茶的皮,用行话叫脆,不禁扎,血管好像也随营养不良而收缩了似的,还不住左右游移,是捐血时最怕遇见的类型。
严明律轻轻拍打着那一寸散布着细密针孔的肌肤,心想这人该给自己扎歪过多少次。
拍打过后血管暴露起来,严明律屏息凝神一针得手,缓缓将抑制剂推入。
严明律常皱眉,但认真时的皱眉和嫌弃时的皱眉是不一样的,到底哪里不一样,林茶却又说不上来。他盯着严明律的断眉想答案,直到严明律喊他,才回神似的往针口堵上棉絮。
“什么时候结束?”
“啊?”
“发情期,”严明律转回身,双手覆上方向盘,“什么时候结束。”
“明天,这是这个月的最后一针。”
“钥匙丢在哪了?”
“不知道,可能落家了没拿出来。”
“粗心。”
这次林茶没有回嘴。他脑里还映着严明律给他注射抑制剂时的画面,从来高高在上的严明律却低下头来。
鼻梁很挺,眼窝深,适合戴眼镜。
他上大课时的确会戴眼镜,黑框,方便他捕捉每一处角落的风吹草动,胆敢睡觉就是死刑。
生化第一节全系大课的讲堂,是林茶第一次遇见严明律的场景。他戴着那副不常戴的黑框,衬着灰色条纹衬衫,两边袖子拉上半截至手腕,露出结实的小臂肌肉。
严明律是衣架子,还是个很会穿衣服的衣架子,只要不开口说话,不知道会成为多少人的梦。
可是他开口说话了,踢走台垫把麦拔高,劈头对着全系就是一句——
“林茶,你把耳朵也落家里了吗?”
林茶第二次回过神来,眼里带着些迷茫。严明律奚落道:“看来脑子也落家里了。”
“你刚问什么?”林茶自若。
“我让你报房东地址给我,要不然你想我往哪条路上开?黄泉路吗?”
林茶泰然自若,边报地址便把针具收回针盒中。
严明律有医院工作经验,本能只信任一次性用品,刚想加以不卫生的指责,脑里又回响起林茶那句穷,还有他臂上细看方能察见的密密伤口。
他不用口服药物,因为这涉及蛋白酶抵抗胃酸变性的新技术,比用针开销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