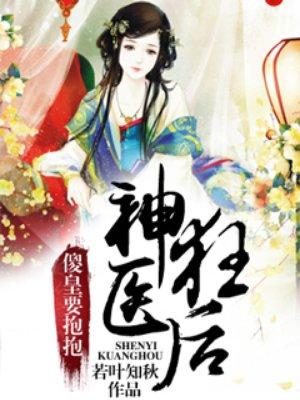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勇与懦夫免费阅读全文 > 第11章(第1页)
第11章(第1页)
薛有年说:“那只能私下里找他谈谈,把误会化开了。”
华临闷声道:“我不去。”
薛有年说:“我去。”
薛有年找那脑残谈了话,回来和华临说谈好了:那脑残愿意卖薛有年一个面子,外加希望以后能拿到薛有年的推荐信。薛有年答应了。
华临倍感憋屈,但薛有年安抚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把事情过去。推荐信也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到时候再说吧。而且,这个圈子说小不小、但说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不是拿了一封信就有用的。”
事后,那脑残还来找过华临,嬉皮笑脸地跟他示了个假惺惺的好,主要也是遵守和薛有年的约定,对华临表个态,保证以后不会折腾华临了,让人放心好好读书。
华临打小就是乖乖牌,虽然这次莫名其妙吃了个大亏,但他还是想着能不得罪这扫把星就不得罪,自我安慰吃亏是福,安全就好,于是敷衍地点点头,算是就此和解。
没多久,华临吃了一大惊:那脑残横看竖看都像花钱买进来的,都不知道能不能无障碍听课,居然陆续提出了好几个令人惊艳的观点,还发了一篇得到了很高评价的论文。
华临和薛有年说这事儿,薛有年平静地说:“人品和学术水平不能完全挂钩。你不用在意他,把自己的学业踏实做好。”
“我知道,不过他……”华临有个很阴暗的猜想,“你说他会不会是有枪手?我就是觉得他肯定没那水平。没道理我现在都写不出来的东西,他能写出来,也太伤害我了吧?他那样子就不像会读书的啊。”
薛有年微微皱眉,想了想:“我看过他发表的东西,确实可圈可点。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谁有那么高的水平,其实也不太可能轻易为了点钱给他当枪手,拿来给教授的话,都能直接收入门了。倒不如换条思路,他家有制药公司的背景,也许那些确实不完全是他的观点,而是他家实验室里研究了很久的数据,近水楼台先得月罢了。不过这些暂时我们是说不清了。”
华临摩挲着下巴,说:“万一是他给的太多了呢?万一枪手正好急缺用钱呢?”
薛有年被他逗笑,眉头舒展开,但很快又严肃起来,说:“你说的确实有可能,不过我们没有凭据,你就不要再对任何人这么说。那个人心胸狭隘,万一又因此记仇就不好了。但学术造假这种事确实令人愤慨,我会私下注意的。”
华临点点头,当时俩人也就没再怎么说这事情了。
直到六年后,那脑残偷、抢、骗、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别人的学术成果占为己有的事情因为某件意外而一股脑地被揭露了出来,连带他家的制药公司也因为一系列相关的违规操作、使用禁用成分等事情而遭到了官方严查,那脑残和家人在牢里吃团圆饭,那时候已经知道了薛有年真面目的华临才意识到,原来薛有年在这等着呢。
不过这是后话了。
当时,虽然那个脑残的事情算是解决了,薛有年向华临保证绝不会再发生,并且华临也搬出寝室,长期和薛有年吃住在一起,甚至上学、放学、去图书馆,薛有年都尽量挤出时间陪他一起,但华临还是很怕。
他的应激反应很强烈。
有一次,他和薛有年去公园野餐,正好好地说笑着,忽然见到旁边一人的冰激凌掉到t恤上,弄得衣服脏兮兮的,他顿时脸一白,胃里开始翻腾。
华临急忙捂住嘴,低着头大口呼吸,许久才缓过来,轻声说:“没事。”
薛有年轻轻拍着他的背,叹了声气:“要不换一位心理医生。”
华临摆摆手:“咱们都知道这种情况看心理医生其实也就是个辅助手段,现在这位挺好的,只是我需要点时间。”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只要有丁点不对劲,华临就浑身难受,无法自控地拿酒精湿巾反复消毒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隔一会儿就漱个口,如果在家就还要洗澡,恨不能把自己搓下一层皮来。
为了搓厉害点,他跑了大半个城市找正宗东北搓澡巾,实在没找到,高价请国内的朋友给他寄过来。他对自己这种行为很无语,但他真的没办法,只能放纵自己继续发神经。
薛有年一开始只是劝他、陪着他看心理医生,直到某天,华临吃着吃着饭就发作了,上楼去漱口洗澡。
他衣服还没脱呢,薛有年在浴室外敲门:“临临,开下门。”
华临忙说:“我没事,就洗个澡,这事不能急,慢慢来。”
“你先开下门,听话。”
华临犹豫一阵,叹了好几声气,还是去开了门,强颜欢笑道:“真没事,再给我一点时间。”
薛有年的脸色很难过,皱着眉头看了他几秒,拉住他的手腕:“出来,我有话和你说。”
华临跟着薛有年出去,坐在床沿上,无辜地看着他。
薛有年叹道:“你不能这么下去了。”
华临心想:我也知道啊,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比你还不想这样啊。
薛有年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让我试试吗?”
华临不解道:“试什么?”
薛有年说:“治疗你的心病。”
华临自己是未来要当医生的人,他绝不讳疾忌医,也很信任薛有年,闻言就笑了:“行啊,我肯定愿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