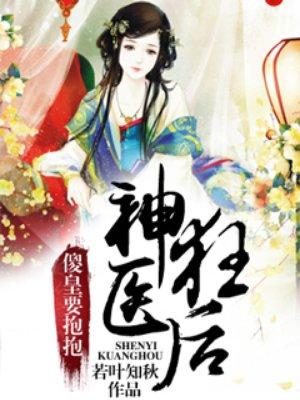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伪娘!delivery > 第16页(第1页)
第16页(第1页)
他吸气再吸气,这握得死紧的手究竟是怒得想要宰了这一群人,还是惊恐得想要捉住身上的人,求闾罗王别收去他的小命,他现在不想细思。&ldo;婶娘向来不是说打喊杀的人,给我查查是谁多嘴。&rdo;婶娘心有不满他知道,但从未做出如此出格的事。&ldo;是,爷儿!&rdo;甜荷畏怯的白了脸。暂窝八王府他全身灼热,像火在烧烤一样,眼前也是一片刺目的光,他合起眼睛,不让眼眶中受辱的泪水流下来。那一天的阳光灿烂夺目,小他一岁的表弟正处于童言无忌的年纪,加上因为是独子,有些被父母惯坏了,什么话都讲得出口。&ldo;你用的都是我爸妈的钱,我爸妈可怜你,才让你住在我们家的,因为你爸爸妈妈都死翘翘了。&rdo;这是事实,但表弟的口气、表情好像施自他多大的恩惠,那握在手里刚拿的一周零用钱不过是少少的二十元,表弟拿的比他更多,但那钱忽然变得烫手起来。&ldo;钱给我,那是我爸妈的钱,你凭什么拿!&rdo;表弟想夺取那二十元,因为他的零用钱花完了,而他既没有高傲的把钱丢在他脸上,也没有卑微的将钱让出去。他受辱的心在刺痛,但他紧握住那二十元,强逼自己咽下就要夺眶而出的滚浸热液。寄人篱下,原来是这么卑微,原来是这么难堪?年纪尚小的他无法自食其力,更无法令父母起死回生,再回到父母身边,做个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只能这么卑微、怯懦、低贱的活着。但有一天,他一定要脱离这种生店!表弟叫嚣得更狂妄,说出来的话更难听,他推开他,拨步快跔,表弟在身后追着。最后他回家时,姑姑和姑丈脸色难看,可能是表弟讲了什么,他没管这些,只是在心里立誓,这一生一世,再也不想要看别人的脸色过活,承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他一直避免动用姑姑他们的钱,从高中就办理助学贷款,尽可能的打工,赚取自己生活所需,这让经济不宽裕的姑姑和姑丈似乎很高兴他的懂事。到了他毕业成年,领到一样建筑奖项时,姑姑和姑丈设宴替他庆祝,表弟没有来,姑姑一直抱怨为什么表弟没有他这么优秀,为什么老是给家里添麻烦,为什么高中缀学也不学个一技之长,又为什么老是交一些坏朋友?他在姑姑眼里算是成功的,但是这是多年来不眠不休、自立自强的结果,他只说了些安慰的话,在某些方面,他还是感谢这两位长辈,他们其实可以这接把他送到育幼院去,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已经尽力了,也许可以做得更好,然而以他的立场,他不能要求。他深知表弟的颓废与失败都是自找的,若是自己都不自爱,那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但是当时二十元的羞辱与痛苦,就像太阳灼烧般疼痛,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ldo;老板‐‐&rdo;他一时不知适这是在唤谁,他是于灵飞,熟一点的都叫他小飞。工地的人会叫他于先生,客户则通常称呼他于建筑师。老板?不会吧,等有一天有能力他会开一家建筑事务所,然后盖一个很漂亮、很大、像城堡的地方收容像他一样的孤儿。他想要笑,却发觉扯动嘴角时,疼痛一古脑的往上激窜,他的背好痛、好痛。&ldo;换药的时候会有点痛,你忍一忍。&rdo;他迷迷糊糊的张开眼睛,一张带点冷冽却又清丽的脸孔出现在眼前,只是向来理智的人儿,现在竟眼眶微红,他动了一下,又是一阵难忍的呻吟,然后才叫出这清丽人儿的名字。&ldo;阿、阿捧。&rdo;&ldo;老板,你伤得好重,刚送来时我还以为你死了。&rdo;阿捧的声音都哽咽了,显然十分担心他,深吸一口气,才慢慢恢复他往日的平稳。&ldo;听说八王爷通晓医药,所以切将军就把你送来这里医治,八王爷开出药方,刚替你上完药,要你醒来时喝点汤药镇痛。&rdo;&ldo;这里是八王爷府?&rdo;于灵飞一怔,随即想通了,若不是八王爷府,阿捧怎会在这里,这个问题简这是愚蠢之至。他记起来了,他被痛打一顿,不过护在身下的小狗好像都没事,他哼哼唧唧的叫痛,随即包覆住阿捧的手,他想起一件重要的事。&ldo;阿捧,现在有人看守吗?&rdo;阿捧愣了一下,显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但还是回苦,&ldo;没、没有!&rdo;&ldo;那好,我带你逃离这里,要让你被那个鬼八王爷给糟蹋,还不如我拼最后一口气带你走。&rdo;他还真说走就走,纵使起身时,痛到脸都皱在一起。阿捧按住他的肩脂,要他躺下来,清冷的声音没有起伏。&ldo;我没见过八王爷,自然也谈不上什么糟蹋。&rdo;&ldo;什么?他不是把你捉来,就是要‐‐要强逼你做一些你不愿意的事吗?&rdo;他大吃一惊。那么大阵仗不由分说的把人从店里带走,不就是要把阿捧给押回来当禁脔,不是吗?阿捧摇头,&ldo;我是被八王爷的五哥给带来的,听说八王爷很气他哥哥这么做,但是他哥哥威胁他,若是我没留在这里,被赶了出去,他就会把我绐杀了,八王爷又恼又怒,却也无可奈何,最后他安排我住在这里,我想要的,他都叫人送来,但从不跟我见面。&rdo;&ldo;这什么呀?他们脑袋有问题,是不是。&rdo;搞什么,把人捉来竟然是软禁在这种地方。对了!以前课本上好像有教过,古代的某国皇室为了血统的纯正,都是近亲通婚,所以生出一堆的神经病,该不会这个时代也是这样吧。&ldo;在这里日子过得也挺好的,就是无聊了点。&rdo;阿捧说得平淡。&ldo;所以,你真的没被怎么样?&rdo;他问得有些犹豫,毕竟这是阿捧的私事呀,他会不会问得太白了?阿捧倒是耸耸肩,&ldo;没,只有刚住进来时,他人隔着门板,站在屋外封我说话,让我不用怕,等过一段时间,他五哥自觉无趣,就不会再插手这事,到时他会派人护送我到任何我想要去的地方。&rdo;&ldo;他站在你屋子外,没试图进来?&rdo;于灵飞瞪大眼睛问。阿捧脸上有点微红。当时是夜晚,他也以为他要进来了,想不到他在外头说完那些话后就真的走了。他打开门,只见到他疾速离开的背影,那背影的确就是那天他在街角帮他抹背的高大男人。他那晚的声音如秋风吟啸,也跟那天一样的温柔斯文,虽然带了点孤傲,却又隐含更多的寒寂,仿佛独自站在高山之巅,忍受无言的风吹雨打。明明是万金之躯的尊贵人儿,为什么那么不快乐?是因为脸上的那个东西吗?&ldo;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rdo;阿捧回神点头适:&ldo;嗯,他连医治你的时候都是在他的院落里,这到没有大碍才让切将军把你送来,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切将军很担心你,一直问你伤势如何。&rdo;&ldo;他是担心万一我死成的话,他就没办法跟我、玩。&rdo;换他睑红了,他也讲得太白了。阿捧轻声笑了,&ldo;切将军好像很喜欢你呢,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会为一个雏儿这样脸色大变,好像恨不得受伤的是他,一会又气恼自己让你遭受这种罪。&rdo;于灵飞听得脸都红了,他急忙摇手,表示情况不是阿捧想的那样。&ldo;这是他家里的人打的,所以他本来就要负起责任,否则我可以告到他倾家荡产,他当然要着急。&rdo;&ldo;按我国律例,打死一个雏儿不算什么大事,他是真的关心你,瞧他以前还说得那么难听,说什么你要陪军营里的都玩过,他才可能有兴致,虽然这样说,结果还是一个好色的男人,关了房门就跟老板玩起来,我去拿尿桶的时候,还见到他全身赤裸的从你的床上醒过来。&rdo;&ldo;什么?&rdo;于灵飞吃惊得差点跌下床去,接着又发出呻吟。哇,好痛,他的背好痛。他噙着泪在心里骂道,这个死男人原来早就跟桃红有一腿,还讲得自己多么委屈清高,看不起他。旋即一股酸酸的,夹杂不悦的滋味也涌上心口。该死的,他是在介意什么,就当是桃红的又一笔风流帐,但……&ldo;我以前跟切以刑睡过?是真的吗?&rdo;于灵飞只差没有大呼小叫起来,阿捧静静的关了房门,查探四周后,才又回到床边,低声却沉静的问:&ldo;你不是桃红姊姊,你到底是谁?&rdo;&ldo;咦?&rdo;难不成刚才阿捧讲的那些话是在试探他?阿捧望着他的眼睛十分澄澈透亮,没有一丝迷茫,好像他已经确认他绝不是桃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