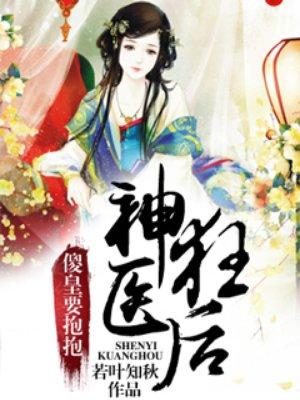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撩表心意什么意思 > 第48页(第1页)
第48页(第1页)
声音还是那么磁性和礼貌,说话的内容还是那么充满噩耗。谷妙语接近绝望地追问:“那我能知道一下,您想起诉我们的名目是什么吗?”陶星宇短暂地笑了一声。声音是好听的,但笑容的成分应该是揶揄和嘲讽。“你们哄骗一个老人把装过的房子再重新装一遍,洗脑的功力很不错,做装修埋没你们了,你们可以去干传销。”陶星宇把这句话讲完,完成了“你想死我就让你死个明白”的义务工作后,再不肯和谷妙语多说什么,直接挂断了电话。谷妙语握着传出嘟嘟声的手机,心里有一片六月的天空在下雪。“我是不是应该改名叫谷窦娥?”谷妙语扭过头,一脸哭唧唧地问向邵远。邵远回给她一片面无表情:“这就是你爱慕的男神?”这么专断、刻薄。谷妙语立刻条件反射般地展开维护:“他平时不这样!他是个随和温暖的男人!他不会动不动张嘴就说发律师函的!”激烈地辩解过后,谷妙语的脸刷地就红透了。“你、你别胡咧咧啊,谁、谁说我爱慕男神了?”邵远冷眼看着她用血气把自己的脸煮红煮透煮熟。他很想告诉她:姐姐,你整张脸都在替你说呢。-------谷妙语没敢去提醒秦经理,最近他可能会收到一封来自业界大牛的律师函。她怕抽抽巴巴的秦经理厥过去。她揉搓着自己的头顶,小丸子给她揉搓得东倒一下西歪一下,无辜极了。耙够了头发,她一抬头,问邵远:“你说是不是陶大爷和陶星宇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什么误差?”在邵远的敦促鼓舞下,谷妙语给陶大爷打了通电话,以确定这个误差的大小和范围。陶大爷在电话那边中气十足地吼:“小谷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开工拆家?”谷妙语:“……”她想这么急切想拆掉自己家的人,全北京恐怕也就陶大爷这么独一份。她问陶大爷:“大爷啊,我想和您问一声,您儿子知道您打算把家里装修砸掉重新弄的事吗?”大爷呵呵一声冷笑:“我和他说了,他不信,非说我是受了你们蛊惑,要告你们。真有意思,我不信他能告!”谷妙语差点失禁了。你不信我们信啊我的大爷!谷妙语赶紧说:“大爷,我刚跟您儿子通电话了,他是真的打算要告我们!”大爷的声音陡然变得欢天喜地起来:“哎哟,真的啊?他真的要告你们啊?哎哟这个好这个好!这小子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现在这么看,他还是在乎我这个老爸的。”谷妙语:“……”她都快饱含热泪了,百感交集喊了声我的大爷啊。陶大爷听完这一声呼唤就打断了她:“得嘞,孩子,你打住,你叫得我起鸡皮疙瘩!你啊,这几天就赶紧和小邵带人来开工,陶星宇要是真敢告你们,别怕,大爷我给你打擂台!你就放心跟他干,干到底,打官司的钱大爷给你出!”谷妙语握着手机的手一个颤抖,手机都差点摔地上。这真是父子吗???大爷还在信心百倍地说:“到时候我去法庭上给你作证去,告诉法官,你才没骗我呢。法官一看我这精神百倍的样儿就能知道,我是清醒自愿的,我比谁心里都门儿清,精神毛病一点都没有,绝对不是被你们骗的。然后我们再当庭反告陶星宇诬陷诽谤,绝对能赢!放心孩子,大爷为你站台!对了你记得赶紧带人过来砸墙,要不然大爷告你违约。”谷妙语:“!!!”又要告?她招谁惹谁了啊……谷妙语听完陶大爷里里外外这一席话,怎么品怎么觉得他精神百倍是有的,但清醒以及精神毛病一点都没有……再议吧。谷妙语夹在陶氏父子中间受了一天的夹板气。她给陶大爷打完电话说明自己要被他儿子告的具体情况后,不多久陶星宇工作室的电话打过来了。陶星宇的助理用平板无波的声音告诫谷妙语:陶老师让我通知您,请不要再去骚扰他父亲。您也是做设计的,设计师要有风骨,才能设计出好作品。谷妙语放下电话问邵远,陶星宇为吗让他助理打电话,他自己怎么不打呢。邵远说:他可能不想跟你说话。谷妙语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一边是老子催开工,不开工要告违约。一边是儿子催解约,不解约就告欺诈老人。谷妙语越来越觉得自己小名叫窦娥,无缘无故就夹在这父子俩中间受上了夹板气。邵远的毒嘴也不放过她。“这还没过门呢,就夹在中间难做人了。原来公公不比婆婆好应付啊。”说着这话时,邵远的长睫毛忽闪忽闪的。谷妙语特别想冲上去一根一根给他拔秃了。临下班前,她苦恼地想,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直接去找陶星宇啊,和陶大爷你是说不明白了,老头忒混不吝。你只能去找陶星宇,和他把一切前因后果都解释明白。”顿了顿,他有点怪声怪气地补充,“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我的谷老师,还犹豫什么呢?楼台和水都给你端面前来了,赶紧踩着楼台去摘月吧。”谷妙语抬头看邵远。他可真像个小恶魔。一只能听到人心里在想什么的小恶魔。-------第二天一早,邵远陪着谷妙语一起向星宇设计工作室进发。路上谷妙语一阵激动一阵怂地进行着情绪的交错转换。邵远最后受不了了,问她:“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呢?”谷妙语说:“倒霉孩子你不明白,陶星宇是我藏在心尖上的人,我幻想过无数次我将怎样和他展开人生的正式相遇,千想万想都没想到有一天会是因为他爹和他掐架。唉!”自从心事被邵远戳破,谷妙语索性不再扭捏遮掩。很神奇的是,那些和大人不好说出口的心底秘事,和小朋友说起来却是没什么负担的。邵远听了她的话,切了一声。那声切里满满都是鄙夷和嘲讽。谷妙语听了很生气,踢他小腿:“你切什么切!”邵远站定。“我切你怂。暗恋是所有恋爱形态中最不值得同情的惨剧。喜欢一个人就该去让他知道,暗搓搓地自己藏着掖着恋能有什么劲?对方又不知道,你只不过是在做自己感动自己的无用功。”朝阳正像个流油的鸭蛋黄,一点点往更高的天上爬。邵远站在朝阳下,修长笔直。他的面庞正朝向谷妙语。他那张脸也渲染上了朝阳的金光,光在他刷子一样的睫毛下打下阴影。多有朝气的年轻人,朝阳的光像是个引子,笼在他身上,催动他身体里青春的、旺盛的生命力快快喷薄而出。邵远站在朝阳下,字字清晰地对谷妙语强调:“喜欢一个人,就得让他知道。假如有天我喜欢上一个人,我一定不像你这样,畏畏缩缩,藏藏掖掖。我会告诉她让她知道的。”谷妙语看着沐浴着一脸晨光的少年人,无限感慨。年轻真是无敌,敢爱敢恨的心思张口就说得出,感情的烦恼在他们眼里简单极了,不过是说与不说、做与不做。没什么可顾虑,也没什么可纠结。该怎么形容他们这种状态呢?似乎可以叫青春无惧。但用少年不识爱滋味好像更加贴切。他还年轻着呢,连校园都还没走出。他尚且不懂暗恋的重量与身不由己,所以才能这样云淡风轻。假如有天他也暗恋起一个人,他一定会懂,暗恋的确是惨剧,但绝不是自己感动自己,而是一种不由己只由心的对感情的坚守。谷妙语看着邵远。她忽然发现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戴眼镜了。她口随心动,立刻发问:“你怎么不戴眼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