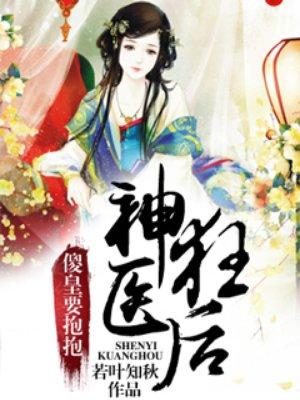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冷血悍将免费观看高清 > 第161章(第1页)
第161章(第1页)
&ldo;克拉克先生。麦斯威尔将军做了一次漂亮的演说,可惜我没有把它录下来。&rdo;
&ldo;你是位老兵,枪炮长,比我懂得更深切。任务很危险。&rdo;
尔文笑了。&ldo;是的,我懂。如果你认为是开玩笑,你也不会单枪匹马地跑来参加了,是吧!&rdo;
&ldo;有人要求我来的。&rdo;凯利摇了摇头,跟着将军走出了房间。
她自己用手扶着栏杆,慢慢下了楼梯。她的头仍感到疼痛,但今天早上没那麽厉害了。
她听到厨房有人讲话,也闻到了咖啡的香味。
桑迪的脸上露出了笑容。&ldo;啊,早安。&rdo;
&ldo;你好,&rdo;多丽丝答道,脸色仍然苍白无力。她走到门口,手扶着墙,笑着说:&ldo;我真的觉得饿了。&rdo;
&ldo;但愿喜欢吃煎蛋。&rdo;桑迪扶她坐在椅子上,递给她一杯柳橙汁。&ldo;我连蛋壳都吃得下去。&rdo;多丽丝答道,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幽默。
&ldo;可以先吃这些东西,不用担心壳的事。&rdo;莎拉。罗森对她说,把一盘普通的早餐推给她。
多丽丝的动作很慢,似乎仍感到痛苦。她很听话,像个孩子一样。时间才过了二十四个小时,现在自然还不会有奇迹出现。她的血压又有了改善。大量的抗生素减轻了她的症状,苯巴比妥的影响几乎已完全消失。最令人鼓舞的事情是她吃饭的样子。她笨手笨脚地打开餐巾,坐在桌边,身穿宽大的睡袍。她没有狼吞虎,而是尽力做出一副严肃正式的模样,在自己身体条件和饿程度所允许的情况下,正正规规地吃完了自己数月以来的第一次早餐。
多丽丝正在恢复,她又成了一个正常人了。
然而,除了她的姓名之外,她们对她仍然一无所知。桑迪端给她一杯咖啡,并坐在餐桌旁边。
&ldo;家在哪?&rdo;桑迪温和地问道。&ldo;匹茨堡。&rdo;那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和女主人的家一样。
&ldo;家还有什麽人?&rdo;&ldo;只有父亲,母亲一九六五年患乳癌去世了。&rdo;多丽丝慢慢地说,接着手不由自主地往衣内摸去。在记忆中这是第一次她的乳房没有由於比利的注意而疼痛。桑迪看着她的动作,在猜想其中的含义。
&ldo;没有其他亲人了吗?&rdo;桑迪不慌不忙地问。
&ldo;我的兄弟……在越南。&rdo;
&ldo;啊,对不起,多丽丝。&rdo;
&ldo;没什麽。&rdo;
&ldo;我叫桑迪,记得吗?&rdo;
&ldo;我是莎拉。&rdo;罗森医生说道,她拿开多丽丝面前的空盘子,又递给她一盘食物。
&ldo;谢谢,莎拉。&rdo;她脸上的微笑依然苍白无力,但多丽丝。布朗已经回到了正常的世界,这是一般人常常忽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是小小的一步,不必跨太大步,只要方向正确,莎拉心在想。她和桑迪交换了一下眼色。这真是奇迹。
没有在场亲眼所见是很难置信的。莎拉和桑迪是从坟墓的边缘把这个女孩从死亡的魔爪中救出来的。一个多星期来,莎拉曾估计也许要不了这麽长时间,一点外界的微小影响原可能在几小时内结束她的生命,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可是现在,这个女孩可以生存下去了,两位医务人员此时曲感受正如上帝赋予亚当生命时的感受一样。她们战胜了死亡,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她们两人才进了医务界。此时此刻的情景又使她们回想起那些她们未能拯救过来的病人,和她们当时所感到的愤怒、悲哀和痛苦。
&ldo;不要吃得太快,多丽丝。长时间没吃东西,的肠胃实际上已经收缩变小了一些。&rdo;莎拉对她说,她又变成了一位治疗病人的医生。现在对她多讲肠道因为突然进食而引起的疼痛和麻烦是没有作用的。没有谁可以阻止她吃东西,她太需要营养,此时顾不得其他方面的考虑。
&ldo;好吧,我已经有点饱了。&rdo;
&ldo;然後休息一下。谈谈的父亲好吗?&rdo;&ldo;我从家跑了出来,&rdo;多丽丝立即答道:&ldo;那时大卫……刚刚收到电报,父亲也遇到了麻烦。他骂我。&rdo;
雷蒙。布朗是琼斯。劳林钢铁公司第叁氧炉棚厂的领班,家住在匹茨堡半山上的顿利维大街,住房为木板结构,始建於本世纪初年。他在工厂上夜班,平时晚上没人在家,显得十分空荡孤独。他的妻子过世,儿子已经战死,女儿晚上通常也都有约会,没有任何牵挂。
他工作一直很卖力,他做了一个男人应当做的一切。但有些事情知道时已经太晚,已经无法挽回。他的妻子当时只有叁十七岁,仍然算得上年轻漂亮。她患了乳癌,动过几次手术,花了不少钱,但病情一直未能见好,反而越发严重,最後不幸死去。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沈重的打击。然而祸不单行,他的独生子又被徵兵去了越南,两周之後战死在那。他开始酗酒,以此消愁。多丽丝也有自己的苦恼,父亲对她的事不了解,也不同情。每当她夜晚回来,看着她衣衫不整的样子,总是对她大加责骂,话说得很难听。
有一天,他突然明白了什麽,驾车来到了警察局,当着大家的面把自己责怪了一顿,希望警方能帮助他把女儿找回来,并答应以後再不责骂她。但是,多丽丝已经失踪,警方尽了一切努力,仍毫无结果。两年多来,他一直与酒瓶为伍,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有两个工友曾劝过他,但收效不大。当地牧师是这个家唯一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