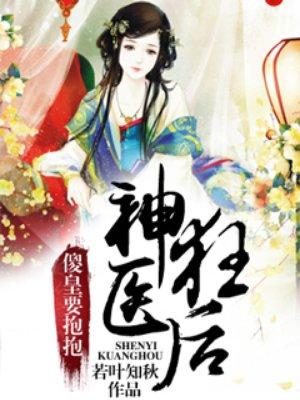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世界知名悬疑 > 第124章(第1页)
第124章(第1页)
&ldo;也许会从天上掉到他脑袋上,&rdo;轻浮的赫勃特说。
&ldo;莫里斯说,事情发生得那么自然,&rdo;他父亲说,&ldo;虽然你是那样祝愿的,你也许还会认为那不过是巧合。&rdo;
&ldo;好啦,我回来以前别动那笔钱,&rdo;赫勃特说,从桌旁站了起来。&ldo;我怕那会让你变成一个自私、贪婪的人,那我们就只好不承认和你有什么关系。&rdo;
他妈妈笑了,跟着他走到门口,目送他上了路,又回到早餐桌旁,以她丈夫的轻信取乐。可这些并没有妨碍她一听到邮差敲门就匆匆跑向门口,当她发现邮差带来的是裁缝的账单时,也没有妨碍她有点苛刻地提到退休的军士长爱喝酒的习惯。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说,&ldo;我想,赫勃特回家来,会有更多有趣的议论。&rdo;
&ldo;尽管这样,&rdo;怀特先生说,给自己倒了一点啤酒,&ldo;我敢说,那个东西在我手里动了;我敢发誓。&rdo;
&ldo;你认为它动了,&rdo;老太太安慰他说。
&ldo;我说它动了,&rdo;另一个回答,&ldo;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我刚‐‐什么事儿?&rdo;
他妻子没有回答。她在观察外面一个男人的神秘动作,他犹豫不决地向房里窥探,看来好像要下决心进屋。她心里联想起那二百英镑,注意到陌生人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光亮崭新的绸帽。有三次他在门口停下来,然后又向前走开了。第四次他手把着门站在那儿,接着突然下决心打开大门走上了小径。就在同时怀特太太把双手放在身后,急忙解开围裙带子,把这件有用的服饰塞在椅垫底下。
她把陌生人带进屋里,他似乎很不安。他偷偷地凝视怀特太太,当老太太对屋里那样儿,和她丈夫身上那件通常在花园里穿的上衣表示道歉时,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接着她以女性所能容许的耐心等待他宣布来意,可他最初却奇怪地沉默不语。
&ldo;我‐‐受命前来拜访,&rdo;他终于说,又俯身从裤子上摘下一段棉线。&ldo;我从毛麦金斯公司来。&rdo;
老太太吃了一惊。&ldo;出了什么事吗?&rdo;她屏住气间。&ldo;赫勃特出了什么事吗?什么事儿?什么事儿?&rdo;
她丈夫插嘴了。&ldo;哎,哎,妈妈,&rdo;他急忙说。&ldo;坐下,别忙着下结论。我相信,你没有带来坏消息,先生,&rdo;他急切地瞅着另一个人。
&ldo;我很抱歉‐‐&rdo;客人开始说。
&ldo;他受伤了吗?&rdo;母亲问。
客人点点头。&ldo;伤得很厉害,&rdo;他平静地说,&ldo;可他一点儿也不痛苦。&rdo;
&ldo;啊,感谢上帝!&rdo;老妇人紧握着双手说。&ldo;为了这感谢上帝!感谢‐‐&rdo;
她突然停住了,她开始明白了这项保证的不祥意义,而且从另一个人躲闪的神色中看出她的恐惧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她屏住气息,转向智力比较迟钝的丈夫,把她颤抖的衰老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屋里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ldo;他被机器卷住了,&rdo;客人最后低声说。
&ldo;被机器卷住了,&rdo;怀特先生迷惑地重复道,&ldo;是的。&rdo;
他坐在那儿茫然若失地凝视着窗外,把他妻子的手握在他自己的手里,紧紧地捏着,就像将近四十年以前他们互相求爱时他惯于做的那样。
&ldo;他是留给我们的唯一的孩子,&rdo;他轻轻地转身对客人说,&ldo;这太残酷了。&rdo;
另一个人咳嗽了几声站起来,慢慢走向窗口。&ldo;公司希望我向你们转达,对你们的巨大损失他们表示真挚的同情,&rdo;他说道,也不看他的周围。&ldo;我请求你们谅解,我仅仅是他们的仆人,只是服从他们的命令。&rdo;
没有回答;老妇人脸色苍白,她两眼直视,听不见她的呼吸声,她丈夫脸上的神色就像他的朋友军士长初次投入战斗时的样子。
&ldo;我要说明毛麦金斯公司否认负有任何责任,&rdo;另一方继续说,&ldo;他们不承担任何义务,但是考虑到你们的儿子为公司效劳,他们愿意赠送你们一笔款子作为补偿。&rdo;
怀特先生放下妻子的手,站了起来,恐惧地注视他的客人。他那干枯的嘴唇动了动,形成了两个字:&ldo;多少?&rdo;
回答是&ldo;二百英镑&rdo;。
老头儿没有感觉到妻子的尖叫,衰弱地微笑了,仿佛双目失明的人那样伸出了双手,接着像一堆毫无知觉的东西那样倒在地上。
在离家大约两英里的巨大的新坟地上,老两口埋葬了他们死去的儿子,回到了沉浸在阴影和寂静中的房子里。这一切那么快就过去了,最初他们简直没有意识到,停留在一种期待状态,仿佛还有别的什么事儿会发生‐‐别的能减轻这个负担的事儿,这个负担对于年老的心是太沉重了。
可是日子过去了,期待让位于顺从‐‐对过去的一切的无望的顺从,有时被误称为冷漠。有时候他们俩几乎一句话也不交谈,因为现在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们的日子漫长无聊,令人厌倦。
在那以后大约一星期的一个夜晚,老头儿突然惊醒,伸出手来一摸,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屋里一片漆黑,从窗口传来轻轻的哭泣声。他在床上抬起身来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