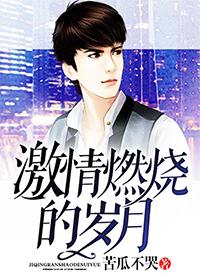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燃灯完结了没 > 第83页(第2页)
第83页(第2页)
一连过了三五天,夜里谢逢殊在床上打滚,嘲溪终于忍无可忍,翻身坐起,话语里带着一点怒气。
“到底睡不睡啊你?”
谢逢殊趴在床上仰头看过去,有气无力地答:“睡不着。”
嘲溪盯着谢逢殊看了半晌,突然冲人轻轻一挑眉。
“既然睡不着,那就别睡了。”
他生得俊朗,五官分明,平日里总是板着脸还好,一挑眉却显得有点蔫坏。他哪有这么好说话,谢逢殊有些戒备地看着嘲溪:“干什么?”
“昨日师父下山,带了一坛酒回来,据说是难得的佳酿。”
嘲溪拿出从小到大诱骗谢逢殊上树下河的语气,压低了声音道:“你想不想尝一尝?”
“哦。”谢逢殊了然地点点头,“你想偷师父的酒喝。”
……孩子大了,不好骗了。
嘲溪接着忽悠:“我是为了你好懂不懂?都说一醉解千愁,没准你喝了酒能好受些呢。再说了,都两百多岁了,没准再过几年就结丹了,还不敢喝酒吗。”
吕栖梧倒也没有不许他们喝酒——都多大的人了。但半夜偷酒喝这种事谢逢殊从来没做过,一时有些犯难。嘲溪乜斜着看他一眼,问:“谢逢殊,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谢逢殊立刻奓了毛,大声道:“谁胆小啊!”
“那你去不去?”
“去!”
吕栖梧和绥灵的屋内都熄了灯,大半夜的,师兄师弟两个人连根蜡烛都不敢点,一前一后摸进了厨房,借着窗外疏漏的月光找酒,一不小心就把碗碟碰得叮咣乱响。
谢逢殊守在门口,听到声音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问:“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啊?”
嘲溪觉得身为师兄颜面有损,啧道:“不如你进来找?”
“我找就我找。”
谢逢殊小心合上门,在黑暗中摸到壁橱,一隔一隔往下找,终于在最底下见到了一坛红布黑坛的酒。
谢逢殊立刻小声道:“找到了!”
嘲溪顺手抄了两个碗,也压低了声音:“走!”
两人一前一后,跟做贼似的——也确实是做贼心虚,说话大气都不敢喘,恨不能踮着脚走路,连开厨房的门都万分谨慎,唯恐发出一点声响。
一开门,便看见一个白衣女子站在门口。
谢逢殊手里的酒坛子差点被他丢出去,幸而下一刻他就看清了眼前的人,小声喊了一声:“师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