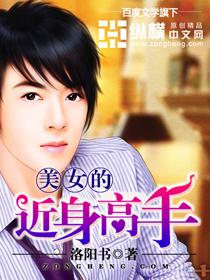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皇叔番外大风刮过全文免费阅读 > 第121页(第1页)
第121页(第1页)
我得到了消息,瑞和的人,前天到了这个城里。可惜我昨天到了时,他们住的那客店的人已经满了,倘若今天再不过去,或许到了明天雨一停,人就走了,再说,雨下得大,晌午时分,他们必定到大厅中吃饭,假装避雨过去,更自然一些。我没走两步,一阵狂风,就将伞吹走了,我折回店中,向小伙计结了所依斗笠,踉踉跄跄向前走,在前方通向码头的街口,忽然间有一人站在风雨中一动不动,像随时要被风吹折了一样,他旁边两个人正拼命要扯他走。我看那人影越看越眼熟,走到近前,不由的喊出声:&ldo;然……&rdo;那人猛地回头,我将斗笠向上抬了抬,&ldo;梅老板。&rdo;我从没见过如此狼狈的柳桐倚,头发衣衫全黏在身上,跟水鬼一样。我扯着嘴角想笑一笑,不知为何却笑不出,只有些生硬地道:&ldo;梅老板……好巧……又遇见了。&rdo;柳桐倚直直地看着我,却是笑了笑,&ldo;是啊,甚巧,又遇见了。&rdo;我将斗笠扣在柳桐倚头上,扯着他回了客栈,立刻热汤沐浴,再备姜茶,谁料柳桐倚还是顿时起烧了,一连两天,吃什么吐什么,他家的那些管事仆人人们只官苦,老管事扯着对我道:&ldo;先老爷就是因肺疾没了,若是少爷也……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rdo;众仆役们齐声呜咽,被我一起轰了出去。夜深时,我拧了块凉手巾,再搭在柳桐倚的头上,我对他说,其实之前那些回,我和他都不是偶尔遇见。我是会到过爪哇。我待在那里一个月,看着满眼的椰子和树上的猴子,我的心中总有一块空得慌。我觉得没有着落。在我这个岁数,之前那些纠葛,是真是假,都如云烟,但有一人,能让我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信,可托,可心安,可相伴,才是实实在在,这个人,只能是柳桐倚。不管他是朝堂之上的柳相,掌管瑞和的梅庸,还是那芹菜巷中,小宅的主人。我把柳桐倚手塞进被子里,&ldo;所以你一定不能有什么,否则将来我真的临到终了时,要指望谁?&rdo;我正要起身去看药锅,忽然听得一个低弱的声音。&ldo;可别再找我了……你吓了我三回……我真够了……&rdo;我擦了擦鼻涕,把伤风药喝下去,门响了两声,柳桐倚的管事走进来道:&ldo;赵老板,我们掌柜的已能四处走动了,说请赵老板一起用午饭。&rdo;午饭十分素净,因为我尚在伤风,柳桐倚也大病初愈,除了一盆奶白的鱼汤之外,饭桌上全是青菜萝卜皮。连米酒,都不能吃。兴味寡淡地吃完饭,我实在没心思再喝茶。我用手扣住茶碗,向柳桐倚道:&ldo;对了,梅老板,我有个事情,想托你帮忙。&rdo;柳桐倚斟茶的手停了一停,&ldo;赵老板请说。&rdo;我道:&ldo;是这样的,前些时日,我做生意赔了点钱,所以……&rdo;柳桐倚放下茶壶,看向我,我接着道:&ldo;我不是和你借钱。是想问你,瑞和里,还有空缺么?比如,二掌柜,管事什么的,你看你这生意越来越大了,事情多,总要多些人帮亲,再有……&rdo;柳桐倚也笑了:&ldo;今日我并不想再绕,却是你,一直在绕。&rdo;十年后,又是五月,我与然思出海办了一趟货,秋时方回,刚到家中,李管事便道,有京城送来的急件,压在这宅中半个月了,指名道姓,要送给我。我与然思从上岸这一路,就看见沿途情形有些异样,一路上也听了些议论,我一看那信的封皮,心中顿时凉了。是启檀的笔迹。我匆匆拆了信,里面只写着几句话,却让我手脚冰凉‐‐叔,皇上病重,想见你一面。(楷体)我从马上一路狂奔,赶到京城外,正看见城军浑身靛蓝,正将丧幡升起。我两眼一黑,便什么也不晓得了。秋雨细密,浸透了泥土,山中红叶,一片触目般红。我挖开泥土,将那青花瓷小瓮埋在碑旁,碑上刻着‐‐德宗皇帝顶骨之碑。我只记得,我侄启赭,,不是什么圣上万岁,也不叫什么德宗。他就是个有些人生的变扭孩子。生在帝王家,规矩多,拘束大,想玩的不能玩,想吃的不能吃,为了礼仪体面,一个孩子长到十来岁,连腊八蒜都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