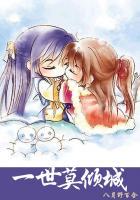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流年未央 经年未忘 > 第六十章 满地尸骸(第1页)
第六十章 满地尸骸(第1页)
玉带桥边若有人家不曾熟睡,半夜起来推开窗户,是否可以看见一群老弱妇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拉动着马车,仿佛是在月宫之上抬着轿子御风而行的仙人。然而那样的洒脱和飘逸,却并不属于我们。我站在最前方,双手抓住绳索,肩膀和手心想必已经都磨破了。但每往前面走一步,我的心都前所未有的欢喜。
我将为他们带去生之希望,这一点微不足道的疼痛,原本算不得什么。
就在可此,那个叫做蝶儿的女孩出声唤我,“姐姐,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我回过头,发现所有人手中的动作未停,但是都期盼的看着我。我们带着这一马车的兵器,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停下了脚步,在玉带桥上四处盼望,最后伸手将府衙的方向指给他们看,“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此刻已经杀进了府衙门外,只不过必然久攻不下。我们要去的地方便是那儿。”
蝶儿踮起脚尖,显然也看见了府衙附近熊熊的火光。她抿了抿唇,有些不太确定的看着我,“如果去了那儿,我们会不会遇上那些坏人?”
他口中所说的坏人,是指那些衙役们吧。我微微眯起了眼睛,即便是在深如浓墨的夜色里,我也能看见其余人目光里露出的些微恐惧。每一个人都贪恋自己的性命,他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现在……不吝于是去送死。
我深深刺了一口气,反问她,“蝶儿,你不是说过,你不害怕的么。有姐姐在,姐姐一定会保护你们。况且,若是他们输了,我们一样也是没有活路的。若真是如此,我宁可死在他身边,也好过尸体分散两地,日后黄泉路上,没有一个可以作伴的人。”这话说的凄凉,然而却并不伤感。
若人有了必死的觉悟,就不会害怕死亡。而除了死,还有一些东西,是让人足以克服这样巨大的恐惧。
“蝶儿明白了,那我们走吧。”她看着我笑了起来,那样小的女孩,不过才十来岁左右。身量尚且弱小,肩头的衣衫早已经被麻绳给磨破了,隐隐有鲜血从里头渗出来。然而即便如此,她却像是个英勇的女战士。
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她身上,仿佛她成了人群新的支柱。我微微笑了起来,这个小姑娘,总是让我觉得很是羡慕。因为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只有满满的自卑和怯懦,从来没有想过改变什么。
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沈碧清了。而小蝶,在今晚之后,只怕也不再是从前的小蝶了。
战争原来是这样残酷的一件事,将人变得面目全非,但即便如此,也不得不走下去。
再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沉默的在空荡荡的崇德城内行走。真是空了,街道上那些搜寻的衙役们都已经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百姓紧闭着房门,生怕被这场城门失火给殃及。然而多么愚蠢啊,那些和他们一同在这座城池内的人正在流血牺牲为之奋斗,这些人却误以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
四周的气氛沉闷而死寂,但是有一种更加诡异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然而这样空的街道,却叫人心底陡然生出不安来。我不敢松开手,只好低着头继续一步步往前走。
就在这时,身后忽然发出了一声尖叫。我回过头去,原来是一个妇人不知看见了什么,浑身都在哆嗦,伸手指给我看,却是一具死去已久的尸体。
我环视四周,这才发现尸体不止那一具,我们行走在边缘处还不觉得,此刻凝神细看,才发现疏朗的星光之下,照耀的却有层层尸体躺倒在街头。
这些尸体死的惨烈,其中有人的耳朵都被刀砍掉了,然而却紧紧抓着身穿朱色官差服饰的男子,用刀将对方的心脏刺穿。
我几乎不忍再看下去,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有过多么激烈的生死搏杀。
有人发出了干呕声,就是刚才吓得跌坐在地的妇人,她的手按住了一个男人的肩膀,却不提防对方的脖颈被人砍了一刀,上面早已经浸满了鲜血。她吓得发狂,几乎快要哭出声来。
所有人脸色都很难看,已经走到这一步,若是有一个人撑不住崩溃了,那么后头的路只会更加难走。我靠近她身边,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她没有吃东西,呕出来的也不过泛着酸味的清水,混在浓重的血腥味里,越发叫人作呕。
“好可怕、好可怕……”她似乎已经被人吓掉了魂,喃喃自语道。
我神色静谧如往常,只是垂眸看着她,“只是死人而已,有什么可怕的。他们都是无意门的人,虽然此刻已经血肉模糊分辨不清面容,但或许你们曾经在茶楼之中遇见过。他或许是个端茶的伙计,也可能只是寻常的茶客,也可能你们从未相识。”
她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我,一时间有些怔住了。
“你的丈夫,也是参加了这次起义,对不对?”我看她的年龄和装扮,只怕是已经嫁做人妇了。果然,她点了点头,只是神情依旧呆滞,“是我的丈夫,我们原本有一个孩子,可是出门玩耍的时候,在路边碰见苏裴安的车队,被马给踩死了。后来我们进了城,我丈夫就加入了无意门,说是要为孩子报仇……”
我听的鼻尖发酸,然而一时间又不敢说话,只得等到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些,这才将她扶起来,“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恨毒了苏裴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是恨一个人,哭是没有用的。”我的声音渐渐变得凛冽,松开了扶着她的手,“你若是看着这些尸体都觉得害怕,那么可曾想过你的丈夫?他或许因为手无寸铁而被人凌虐,他若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就可以在战场上活下来。”
她直勾勾的看着我,瞳孔里终于有了几分神采。半晌后,她忽然大哭起来,“我的孩子,我的丈夫……他会不会也死在了这里,会不会?”
素洁的月光洒落在我们的衣袂上,这里每一个人都仿佛穿上了一件丧衣。是为了自己所爱之人,还是为这满地忠烈的尸体?
我仰起头,伸手指给他们看,“你瞧,那里便是衙门了。若是我猜的没错,到了那儿,就能看见一场混战,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自己要见的人,或许永远也见不到。可如果因为恐惧而在这里停下了脚步,那么这一路走来,就全都作废了。”
一群老弱病童能够走到这里已经十分不易,我不能在最后一步停下来。
街上铺满了尸体,我也顾不得这许多,尸体又算什么?只要能够见到森爵,就算地狱火海我也一样要去。我第一个俯下身抓起绳索,继续往前走,然而因为所有人都撒了手,不敢从尸体和血水上走过去。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拉不动这样重的马车。
而且肩膀必然早已经勒出血痕,歇息了这片刻,此刻再用绳索来勒,简直叫人痛不欲生。然而我始终紧紧咬着牙关,不肯露出半点痛苦呻吟。这些躺倒在地上的尸体,他们就连感受到痛苦的机会都已经被剥夺了。在他们面前,我又有什么资格埋怨?
我咬牙将绳索在自己胳膊上绕了两圈,每一步都仿佛是要将自己的手臂生生给拽下来。然而才走了两步,只觉得后头的力道似乎小了不少,一开始那个呕吐的妇人站在了我身后,还有那些茫然失措的人都站了过来,重新将绳索捆在自己身上。
我此刻就像是一个领头人,然而引领着他们要走的这条路,究竟是到达彼岸,还是会在路上溺死,就连我自己也无从得知。
然而我想起森爵临走之前的笑容,他的目光坚毅,是不破虎狼终不还的气概。那张脸让我的心口滚烫起来,前路艰难险阻,但我并非是没有目的的游荡,正因如此,我再次蹒跚前行,每一步,都踏在血肉之上。
越接近官衙我就越发觉得紧张,因为前头战况如何,谁胜谁败,我无从知晓。甚至我都都开始怀疑自己所指的这条路,究竟是不是对的?
但是我不能说,这所有的慌乱和无助,不能向身后的人倾吐。他们此刻都在凝望着我的背影,我是一盏微弱的灯火,若是连这点灯都熄灭了,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马车发出辘辘声响,像是一声又一声的咳嗽。越靠近官衙,我的手心仿佛除了磨破皮渗出的鲜血,还有因为紧张而滚落的汗水。我不由深吸了口气,眼前的一切也变得模糊起来。脚步声仓促而凌乱,有人从长街里显露出身形来,“什么人?”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身后却传来了一声尖叫,“哥哥,哥哥是你么?”原来是蝶儿,她飞奔着往前,像是一只可怜的小兽扑进对方的怀里,“蝶儿?”对方有几分迟疑,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几乎快要跪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