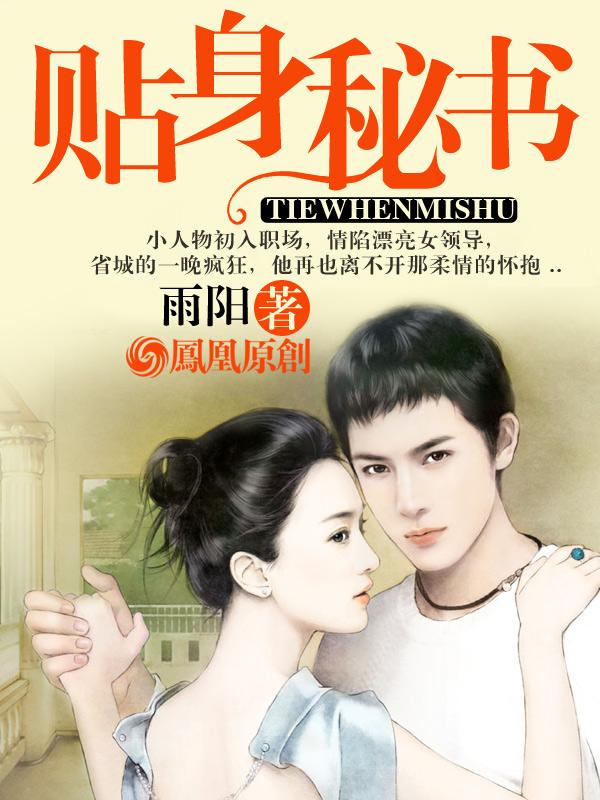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的美利坚魔幻人生txt > 第446章 好了好了别叫了(第3页)
第446章 好了好了别叫了(第3页)
“忒弥尔女士,您好!”
助理有些惊讶的发现,迈克·蓬居然隔着电话在躬身致意。
老兄,至于吗?
“我到华府了,来见我。”
“是!”
“她是什么人?”
这种问题,助理一般不会问,但她实在太好奇了。
迈克·蓬弯腰洗手,意味深长的说道。
“themasterofcountry。”
美利坚国家政务院的厕所玻璃非常干净,女助理可以看清镜子中迈克·蓬那复杂的表情。
她感到有些心神摇曳。
——西洲物流,格鲁总经理正在听手下汇报工作。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酒杯,手里拿着麻草烟,整个人垮的就像一个废物,而非一家大集团的总经理。
但凡西洲的股东们稍微关注一下事实,可能都会炒了格鲁。
可惜,西洲的股东们关注的点不在于格鲁的行为会不会给这家物流集团带来不好的影响。
成总和蜜儿不关心治疗手段,只看疗效。
“你是说,我们在三个州的分公司都遭受了佛伯乐的调查?”
警长先生放下了麻草烟,认真的问道。
“是的,仓库问题、驾驶员注册问题等等,其实这些事大家都在做。
但显然,我们被针对了,格鲁先生,在我看来,这不属于佛伯乐的职权范畴。”
格鲁笑了笑。是不是佛伯乐的职权范畴,他可太清楚了。
纯纯是报复罢了。
“我知道了,你继续和佛伯乐的相关负责人沟通,先试试能不能在具体事件的层面上把麻烦解决。”
下属有下属的工作,格鲁有格鲁的工作。
具体事物层面的问题不是重点,麻烦的真实面貌是,佛伯乐对格鲁的反击。
别闹了。
法律只是工具,佛伯乐借工具打击西洲,问题不在于工具。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机构是工具的延伸,没有多少独立性。
特务机构作为美利坚国家强制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具属性之余,又有着某种特殊性。
答案是没有。
忠诚是种奢侈品,个人的忠诚多数时候都不太可靠,更别提组织的忠诚了。
如果佛伯乐找得到强有力的理念强化组织性,实现了忠诚,最睡不好的人估计是美利坚的资本家——尤其是闪米特流浪者资本家。
属下离开,格鲁拨通了胡特的电话。
“胡特,怎么回事?”
“给钱!”
“佛伯乐的人像疯狗一样,在好几个州查了我们,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给钱!”
“伙计,我们是朋友,帮帮忙!”
“贱人,给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