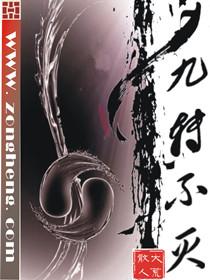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柳舟记 > 第50章(第1页)
第50章(第1页)
“拿来。”赵宜芳接过信扫后,笑了声,“说是要请皇命赴西北,哪怕做个参军司马也要帮我。”
“他来怕不是帮衬,一张嘴不晓得要惹多少事。”离昧知道那“夺锦”二字出来后,一时京城兴起一股押赌风,众人都想看承了商王衣钵的锦王究竟花落谁家。
赵宜芳却在被皇帝训斥时不服道,“可宜芳并非菟丝女萝,也非流水桃花。”她不落谁家,也不为谁所夺。祖母打小儿教养她都是自成自敬,不谄不曲。
“让他来。京城里还有多少想攀龙附凤的,尽管来。不捏住他们本王还不好化缘。”赵宜芳“哈哈”一笑,对着铜镜再照了照。
三州安抚使也不好打正门里出,来来往往的客商四民,甚至还有北夏的细作都暗地里留意着这座府邸。一身常服、无钗环点缀的锦王提着还热乎着的北食就像个王府寻常管事的。她直奔县衙和书院,发现谢蓬莱都不在。
转到县衙后的夹院只见院门紧闭。里头倒传来声声谈笑,赵宜芳只听见一个男人道,“打西头往沙海走了五个多月,还是头一回喝上这样的酒。谢大人才是真海量,空现佩服。”
陪自己几杯就倒,陪别个海量不说,还谈笑风生。赵宜芳俏眉几乎倒立,手里提着的东西不晓得该送进去还是拿走好。
“头陀自谦了,这是‘紫雀’里卖得最好的,沙海人喜烈性酒,没想到你打京城里呆惯了的也喜欢。”谢蓬莱继而问道,“北夏人这些年酒水不晓得耗费几何?”
“本朝进贡的自然不够。”那自称“空现”的头陀说话也并不照顾本朝面子,“北夏人多用高粱酿酒,现无论夏京街市,还是边疆村寨,都能看到酒肆。”
赵宜芳听了会,才意识这二人并非只谈酒,西边诸邦的风情地貌,贵胄升迁都随意聊起。她将那几包吃食挂在门环上,随即拍了拍门后即快步离开。
“谁?”谢蓬莱好奇地打开门四处张望,看见了门环上的东西。拿在手里是热的,嗅了嗅后她面上微喜。“怕是我那调皮徒弟见我有客不好打扰,送点吃的就走了。”边说边打开时她却惊呆,这烹饪撕泼的手法可不是锦王府上的?
坐她对面满面虬须的黑面头陀却笑,“这是谁知道头陀是酒肉穿肠过?”
谢蓬莱将吃食放在他面前,笑道,“怕是。”心却波摇水萦起来。来人怕是锦王,听到她有客后便离开了。锦王为人虽然霸道直接,但也有如此雅致体贴的时候。
论及体贴,从穿衣吃饭,到问政施策,锦王对自己已不仅仅是知遇之情。数年前济北郡的玲珑女童,果真会因为一场诗会而挂记至今?
“谢大人有心事?”头陀抓了羊肉就往嘴里狂放地塞,揩了胡须后笑盈盈地看着数年前认识的老友。
“头陀何以见之?”谢蓬莱也不掩饰,掩在杯口忽然笑了。
“一波愁牵千里远。头陀虽然不知人间□□,但晓得这包肉不简单。”空现吃得满嘴油花,“好吃,这是正宗的北食做法,没想到沙海来了这样厉害的厨子。”
厨子厉害,但能看出谢蓬莱千里远的愁绪更厉害。谢蓬莱安稳下来,继续陪着空现吃喝聊天。
赵宜芳则在街市上四处转悠,花巷的瓦舍里不少人认她,便不方便随意找柳秦桑听琴。酒巷却是好去处,偶尔听听巷议也有收获,那句“夺锦天子门生”就是在酒楼里听到的。
“紫雀”的酒的确烈,能让谢蓬莱青睐的她愿意尝尝。赵宜芳到时里面已到了午客最多的时候。无奈之下和人拼了桌,坐定后发现正是一个人抓着脖子喝闷酒的云白鹭。
“看来侍读这活计还是太散闲。”赵宜芳用眼神示意云白鹭别声张,云白鹭就给她斟了杯,“下了学去找师傅悉心讨教,却看见师傅陪着个脏兮兮的头陀在那说得兴起,还嫌我碍事。”空现她曾有过一面之缘,但并不熟悉。
这也是在谢师那儿吃了闭门羹的。但选日不如撞日,暗猜不如询人,“谢师为何还是单身一人?”
云白鹭笑着摆手,“我也想不明白呐?我爹以前还曾给谢师说亲来着,她也不愿意。不过不答应是对的,那个参将早就死了,不然连累谢师做了寡妇。”
赵宜芳转身给她换了更好的酒,她目光灼灼盯着云白鹭,“谢师是不是喜欢女子?”
云白鹭扭过脸,“我不敢猜。这得您去问谢师。”一张脸被锦王揪住了耳朵,赵宜芳皮笑肉不笑,“难不成真是你?”
一口酒差点喷出,云白鹭急了,“怎么可能?我……我是”,这会儿不是,可早晚得是月娘的。但瞧锦王为了谢师急赤白眼也是稀罕,云白鹭只卖了个关子,“谢师钦慕的一男一女……都过世了。”
明显见锦王松了口气,有连着饮下几杯烈酒,一时没顶住酒意,赵宜芳揉着头,“不去世,本王也要谢师做寡妇。”
云白鹭倒吸了口凉气,“那不行,醮夫再嫁谢师未必愿意。”真要是进了锦王府,皇帝也第一个不答应。民间女子结契就罢了,皇家体统脸面摆哪里?
“本王也是寡妇,扯得平。”
云白鹭终还是喷出了一口酒。
第40章
书院修整时,城里客商的叫苦声也早传到了谢蓬莱耳中。开门才是做生意,关门不让货进人出三两天可以,快一旬就让人憋不住要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