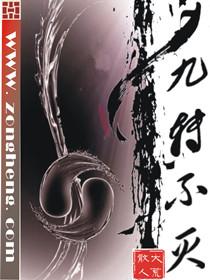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潮水连海平 > 第39页(第1页)
第39页(第1页)
“你疼也活该,谁让你那样对我,谁让你不要我……”说着说着,我竟然傻乎乎的开始流眼泪,泪水很快划过脸颊,一滴滴的滚落。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为什么在哭,只觉得茫然又毫无头绪,伤感,难过,痛苦,心疼,还有一点点的惊喜,全搅成一团,心乱如麻。他没有解释,也没有争辩,只是像以前一样,温存的抚着我的背,用指尖帮我擦眼泪,那熟悉的触感,夹着他略带苦涩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已经根本无力思考。“越越,是我活该,我已经犯过一次天大的错误了,以后再也不会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他在我的耳边喃喃地说,我能感觉一团团微弱的热气拍在耳后,理智早就随着眼泪不知所踪,脑子里,竟然开始胡思乱想。小时候开始学古筝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这个孩子的手又小又软,心地肯定也很软。我一直不觉得。即使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可很多时候,都是妈妈听我的话,大到上什么学校,小到晚饭吃什么菜。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坚强独立的孩子,连上大学的四年,都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没有犹豫踌躇。直到遇见海潮。“晚上下了班我来接你。”早上,海潮送我上班,站在车边,不肯放我走。“好。”我点点头。即使辞职,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他的手上,还有大把雪季的股份,还有很多工作要交接,这两天尤其的忙,却总是要我在琴行等他一起回家。“越越,乖乖的等我。”他看着我的眼睛,深邃的眸子,几乎要直看到我的心底里去。“当然。”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这样的抽身而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不催他,也相信他能处理好一切,回到我的身边。早晨的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辗转着照在他的头顶,整个人笼着一层淡淡的光辉。他翘起嘴角笑笑,弯腰亲了亲我的脸颊,转身拉开车门,准备上车。“等等。”我叫住他,蹲下去帮他绑上松开了的鞋带。“好了。”我直起身来,看他坐进车里,对我摆了摆手。他的车绝尘而去,我刚打开琴行的门走进去,收到一条短信。越越,这次我总算没做错事。我笑笑,他像还是害怕我不肯相信他一样,这两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种不太放心的恐慌。其实,从他说出“我只要你”的时候,我早已经再也没有办法不原谅他。只是,我怎么能轻易的放过他。“可是你还是没告诉我为什么不要雪季要我啊。”短信发出去,足足等了半个钟头,他才有反应。“雪季本来就不应该是我的,老天已经惩罚过我一次了,我不想再为了不属于我的东西,放弃一切。”跟他这几天说过的话,没有什么区别。我只好摇摇头。下午新到了一批红木的琵琶,量不大,但是因为品质上乘,所以分量都不轻,我一个一个的抱在怀里试过来。前两年因为比较空,我跟刘黎学了一段时间,加上古筝的基础,还能玩的像模像样,挺能糊弄人的。几把琵琶试下来,腿都压得酸了。把琴都收好以后,我看见琴行的门边有人在等我。“张老师,那个人从你开始试琵琶的时候就来了,一直等到现在。”小李站在收银台后面对我说。那应该是个年轻女子,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风衣,身材修长,只是背对着我们,看不清楚脸。“我去看看。”我走到她的身边,她听见有人过来,转过身来,只看一眼她的眼神,我就反应过来她是谁。“你好。”我对她伸出手。“你好。”她有礼貌的伸出手跟我轻轻握了一下,立刻放开。我们都心照不宣。“过去坐吧。”我指指门边的桌椅。她走过去坐下。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优雅得体,就像她脸上的妆容,淡淡的,衬着明艳的五官,走在路上,肯定有不少人要回头看她。我泡了杯茶,让小李先回家,就走到她的对面坐下。我向来觉得自己是个镇定的人,只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我竟没有一丝慌乱,还是有些意料之外。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杯子,看了很久,才开口说:“你知道我是谁吧。”我点点头,却发现她一直没有抬起头,只好又说:“知道。”她不再说话,我只觉得沉默的尴尬,好在琴行里有低回的音乐声,倒不显得太过安静。她像是思考了一会,抬起头来对我微笑了一下:“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海潮会那么喜欢你,今天看见你,我忽然明白了。”她的笑,像是训练有素,例行公事一般,我知道,她对着我,哪里还笑得出来。我没有接话,她自顾自的继续说:“你应该可以给他家的感觉,我就不行。”她说的话,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女人的感觉,一向很灵敏。“我第一次见到海潮,是在法国。我们两家是世交,那年爸爸带我去法国玩,海潮的爸爸也去了,我们一起去他的学校找他。那天太阳很好,天气很热,他在学校的球场上踢球。场上都是黑人,个个人高马大,可是他在里面,还是最抢眼。他好像一点也不害怕那些又高又壮的黑人,跟他们抢得很凶。球踢完了,他满身的汗,却一点也不显得狼狈,笑得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