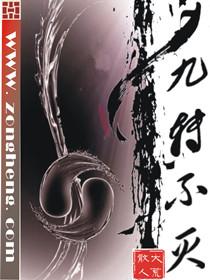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同路人美剧双男主 > 第57章 人情事故三(第1页)
第57章 人情事故三(第1页)
单文静用余光看着她,这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孩一直陪着自己,只是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本以为这个人最多就是象征性的陪自己坐一会,便会自行离开,她就放着没管,她也没精力管。
张伟倒下了。住院、生活、未来、钱、工作、家庭、等等所有与现实有关的东西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她哪里还有其它精力。
以至于自我暗示般的,愿意相信这扯谎一样的话。
她回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和张伟有关的事,这个总是大笑着的人,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曾有人劝过自己,说“这个‘外线’男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出息、他就是个粗糙野蛮的傻大个、唯独占有欲强,到时候钱、又随时家暴你,和他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大个就一定要傻么?
才不是这样,其实他心思很细的,很多事他看得比别人都清楚,只是多数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他知道谁想骗他,但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因为他同样知道多数人忌惮他天生的身形,不敢欺骗他。
魁梧就一定要凶恶么?
那当他们一起在内线吃亏的时候,在自己因为他被内线人歧视、而气的得直哭的时候,他的哈哈大笑又是什么呢,他温柔的劝说自己不要生气时的担当又是什么呢?
——回过神时已经深夜了。她仍坐在身边陪着自己。
她与大伟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单文静接近自言自语的嗫嚅:“可以问你一件事么?”她说出口时就后悔了,只希望对方没有听到自己灰尘般的声音。
对方的声音也很轻柔,却总有股说不出的野性:“什么事?”
“你和。。。张伟是什么关系?”
“我俩,大张伟是我铁子。入职就基本在一起干来着,他人虽然虎点,冲动了点。还是不错的,该怎么说呢,我俩也算是过命的交情吧。”
铁子。大伟总是会和其他的人称兄道弟,他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呐”。但他从来不会把这些“铁子”介绍给自己。大伟没有真交心的人。
她心里有些难过,语气也哀怨起来:“我没听他说过还有女性的铁子。”
“呵,我的情况是有些复杂。”
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一定是有所隐瞒。但自己还是选择相信大伟。
他会背着自己喝大酒;背着自己打群架;会隐瞒自己受伤;骗自己没吃苦、没吃亏;但他绝对不会劈腿。
尘看着刚说几句话又沉默的单文静犹豫着问了句:“你和大张伟是怎么在一起的?”
自己和他是怎么在一起的?好像认识他好久了,回想起来缘由来。。。却像是昨天才确认的关系。
尘看着她又沉溺在回忆中离岸边越来越远。
良久过后、她才吐出一句心声:“在他眼中,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女人。”
“哈。”尘轻声笑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像那老匹夫能干出来的事。”
瓷器一样的单文静,她气场看起来是脆弱的,似乎只用指甲这么轻轻一刮、就会像钥匙尖一样、带着刺耳的声音、在这天青瓷一样的女人身上留下永久的白色划痕。
多数男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是个弱女子,我该保护她。
正因为她是个弱小女人,所以我就是那个强大男人。我要把我最好的都给她,我要看护住她,让她待在精心搭建的美丽又安全的雪花球中。不然什么都不懂的她就随时可能会受伤、会痛苦,我也会一起难过。
所以我为了你好,你就要听我的,因为我是爱你的;为了你好,那我的喜怒忧悲,你都该接受、该理解,你该感到幸福才对。我都是为了你好,因为你是小女人,是没见识的、怯弱的小女人。
大张伟不是这类人,在他眼中人人是平等的。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常明的灯无言俯瞰众人。
——墨色的夜仍在窗外低语。
陪护的家属们坐在褪色的蓝塑料座椅上疲惫的打瞌睡,有的则躺在大理石地板上,就地打铺。
这空间里偶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偶有三三两两的人去。他们的脚步声踩在地面上又弹起来,踢踢哒哒的像是在敲击冰凌。
慢悠悠出来的人身上固然是冷的。但急冲冲进去的人更是一种别样的冰,你的心情有多么的焦急也是不可能融化掉它的。只会让它冻得更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