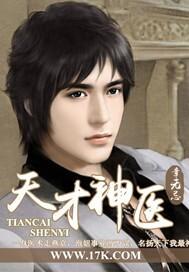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明月照我作者 > 第137页(第1页)
第137页(第1页)
明镜司方面不曾为此许诺过好处。但谢慈不是个善人,费心费力必然有所图谋。他所图的唯一不用他自己动手去取,而明镜司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益处。刑案上,再也不是刑部的一言堂。督察院,大理寺,与刑部三司的地位不再稳固,是用明镜司撬开的缝隙。当年,明镜司崭露头角的时机,正好就是谭大人一家人枉死之后。谢慈将那张写名字的纸挂在屏风上,正对着脸,沉下一口气:“霍春雷,出身武将,他父亲是前朝唯一擅长水战的将军,希望不要这么荒唐……”芙蕖和他同一个姿势,抱手现在屏风前,在一片胡乱晕染的墨迹中,又发现了一个处在最中心位置的名字。季博远芙蕖摸着自己的下巴:“这位是……传说中的内阁首辅吧。”自从谢慈入阁后,传说中内阁首辅就成了个摆设,告了病休,一切事宜都由谢慈这个次辅主张。季博远几乎没有再露过面。芙蕖嘴巴很毒:“此人现在还活着吗?”谢慈瞪了她一眼:“别乱说话。”芙蕖觉得他的反应很有意思。“听说季首府是当世鸿儒啊,弟子万千,你也曾听过他讲学吗?”谢慈道:“我是在扬州读的书,季首辅一下江南便水土不服,我们俩从前没见过。”芙蕖问:“那你为何要把他的名字挂上去?”谢慈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我总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无辜。”他可能是出于一个久居高位的人对同僚的揣测。能站在朝一品官员的位置上,对于当下的时局不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往深了去想,芙蕖实在是稚嫩。当官的心思她不懂,能窥见一二分就已经算是敏锐了。谢慈一路上火烧眉毛一般的急迫,最终换来的是不到一日的安宁。正午刚过,明镜司押着人回燕京了。一纸口供递入宫中,呈到了皇上的面前,便也等同于呈到了谢慈的眼前。皇上看着纸上的名字一言不发。谢慈道:“多热闹啊。”燕京道上,赃污狼藉的,通敌卖国的,谋图皇权的,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掺合进去乱七八糟搅和的。几乎所有人都躺进了这一滩浑水中,等着看明天的太阳从哪个方向升起。“皇上永远是皇上,臣子永远是臣子,您是一个王朝的根,我们都是傍您而生。皇上您若是立不起来,我们就算是长到遮天蔽日也只是一根藤而已。”“可朕想当仁君。”“皇上当真仁义,以身伺虎,日削月割,百姓的姓名都可拱手让出成全您一世贤名。”皇上脸上有些难堪:“先生,别这样说。”谢慈接了名单,也贴在屏风上。皇上望着那满目疮痍的两张纸,可能一时尚未意识到那繁杂的线条都意味着什么。直到赵德喜碎步跑进来向皇上禀告:“陛下,霍指挥使求见。”谢慈撇了他一眼:“霍春雷能把你吓出一头汗?”赵德喜可能是真吓着了,从谢慈的角度,能看到他颤抖的下唇。他说:“霍指挥使是带着人来的,现已将朝晖殿围住了。”皇上霍然起身。谢慈一把按住赵德喜的肩膀。赵德喜双膝一软,差点当场磕下。谢慈说:“稳住,他带了多少人?”赵德喜说:“二十余人,趁着城门换防的间隙,凭借陛下您的特赦令牌,堂而皇之进来的。不仅没有受到阻拦,也没有惊动禁军。”皇上心里有了不妙的猜想,不敢置信:“霍指挥使不会的。”沉稳的脚步声已经靠近了门外。霍春雷扬声参拜:“臣明镜司指挥使霍春雷,有紧急情报求见陛下!”谢慈不发一言,掉头就退回了屏风后。他像一道沉默的影子,皇上从他的表情中理解了他的意思,稳坐在龙椅上,抬手:“宣。”朝晖殿太空旷了,往日里总有宫娥和内监如众星捧月般的拥簇在皇上身边。而今一个人没有,只一个伶仃的赵德喜,佝偻着背侍立在下。明镜司指挥使当朝二品大员,一身朱玄的官袍上绣着半张狮子的脸,以金线绣其眼珠,耀目夺辉。皇上望着他,道:“明镜司呈上的名单朕已过目,霍指挥使还有何事奏报?”霍春雷年纪不老,四十许的年岁,却长着一张精神勃发的脸,不蓄须,身形骠悍利落。他转了一下头,目光直直的望向皇上身后的座屏,问道:“是皇上您亲自过目,还是另有其人借皇上的名义指点江山?”皇上沉了脸色:“霍春雷,你拿朕当什么?”霍春雷无惧:“臣所说的,是朝中同僚的肺腑之言。前几日,扬州城外劫杀南秦公主的刺客落网,谢次辅设局,明镜司配合,最终供词呈到了皇上手里。自从那些刺客入京的那一刻起,皇上您与谢次辅之间那层牢不可破的关系,便已经公诸于天下了。”他们可以容忍皇上一直软弱好拿捏,但是不能容忍皇上一直被拿捏在别人手里。皇上坦然说了句实话:“朕确实是一直深信谢先生,那又如何?”霍春雷回答:“冒犯皇帝是谋逆,清君侧是忠义。”皇上:“那么,谁要清君侧?谁想当这位忠义之臣?”皇上此刻也后知后觉的想明白了。霍春雷只带二十几个人进宫,是做不了所谓的忠义之臣。谢慈之所以暂避,是还在等时候,确切的说是在等人。霍春雷躬身道:“明镜司自成立之日起,顺天意,从皇命,不论朝局,不掺党政,只忠于皇上一人,而今日无论是谋逆,亦或是忠义。臣率明镜司誓死护卫皇上周全。”皇上点头,说了几声好,道:“如此说来,霍指挥使是有可靠的情报了?”霍春雷直视皇上的双眼:“陛下,你实在是信错了人。”苏戎桂在府中吃完了女儿亲手奉的茶,换上了官服。苏慎浓放置好茶杯,问了句:“父亲要进宫面圣?”苏戎桂点头说:“京中又有案子了,皇上此刻应当证交头烂额呢,为父不放心,想去看一眼。”苏慎浓没有觉得异常,叮嘱了几句,路上小心,便端着茶具出门。然而刚走出门外,便见到兄苏秋高也一身整齐,腰间还配了剑,在外头等候。,苏慎浓也说不清为什么,在兄长转脸过来的时候,她下意识的缩回身子,往柱子旁边躲了一下,错开了苏秋高的视线。似乎是她身体的本能告诉她要这样做。苏秋高在门外等到了父亲,父子俩一起相携上了马车,苏慎浓躲躲闪闪,在他们动身上车的那一刹那,看清兄长腰间粗布包裹下,露出了一截明黄色的穗子。——那不是普通人的配剑,先帝御赐的尚方宝剑!苏秋高一介布衣,连皇宫的门都进不去,哪里有面圣的资格。马车载着父子俩往东边驶去。苏慎浓手中还端着茶具,在门口的寒风中站了良久,猛然间身上一个激灵,浸透了冷汗的衣衫被风吹过,令她手脚既发冷又发寒,紫砂的茶杯落地,碎开了裂纹。苏戎桂在车里拍着儿子的手臂,说:“咱们的皇上,可以温和,可以软弱,可以谁都不信,但他不能只专信于一人。”苏秋高:“我明白父亲的意思。”苏戎桂:“谢慈人不在燕京,或许还在扬州,或许在回京的路上,等我门说服了皇上,在他踏进宫门之时,就是诛杀他的最好时机。”苏秋高脸上的神色却一点也不轻松:“可是父亲,若是我们不能说服皇上呢?”苏戎桂闭了一下眼睛:“那为父只好祭出尚方宝剑和先帝的遗召了。”燕京今年还没有开始落雪,但已经四处都是霜染的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