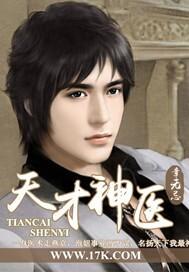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明月照我作者 > 第28页(第1页)
第28页(第1页)
盈盈方乱了分寸:“你中毒了?”谢慈冷淡道:“剧毒……我的命硬,它啃不动,但你就不一定了。去洗了。”盈盈不敢托大,急忙跑到破庙门口,蹲在槛内,用外面泥洼里的积水把手上沾的血冲洗干净。可就在她低头冲手的功夫,余光瞥见了雨点落下时,在水面上晃动不止的涟漪。她盯着那波纹反应了须臾,女人特有的感觉漫上心头,只觉得不妙,她当即顾不上脚下的泥泞,趴下身子,将耳朵贴在地面。在杂乱的落雨声中,她分明辨出了那混杂在其中的密集马蹄声。——“主子!”盈盈跪爬起身,回头便喊:“有、有追兵……主子?”谢慈头靠在菩萨像上,已经全然没了意识。盈盈疾步冲过去拉他。可随即她便反应过来,来不及。听那马蹄的动静,追兵马上就到,往山上路难走,往镇上一马平川,她带着重伤的谢慈,怎么都逃不过被捉的命运。石火电光之间,盈盈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将谢慈移到了后面,用杂草掩了痕迹,拿起堆在一旁的黑布油衣,解下门前棚下的两匹马,冲进了雨幕中,等远远望见黑压压的一群身影,盈盈奋力在马臀上一抽,两匹马嘶鸣着,一前一后奔向了山上。自从进入了冀州,谢慈的行踪便难以摸清。纪嵘也不能确切的探听到他的位置。但他们发现,进入了冀州境内,那些追杀他的人倒是越发的肆无忌惮。芙蕖隐约觉出不妙。既找不到正主的去向,纪嵘和芙蕖决定暂且咬在追兵的尾巴上。杀手们如此张扬行事,总会露出行迹的。果然。前方乱象起。纪嵘道一声“不好”,纵马就追了上去,芙蕖却敏锐地嗅到了藏在雨中的那股丝丝缕缕的异香。她的目光锥子一样,望向那座破庙。略一耽搁的功夫,纪嵘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中。芙蕖的马停在破庙的门前,她跃下来,靴子踩得雨水四溅,落地却静悄悄的。破庙的两扇木门在风雨的鼓动下,互相撞在一起,仿佛随时都能散架。芙蕖伸出手指,轻轻推动一条缝隙,目光向下扫,便见一条极细的银丝嵌在门上,在晦暗处闪烁着冰冷的锋芒。芙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知道自己猜对了。谢慈身边那个女人行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匆忙离开还不忘给庙里留一机关。可他究竟伤到了什么程度?连逃命也没有余力了么?芙蕖对着那一线银丝犯了难,情急之下,必是杀招,凭借她稀烂的身手,万一死在自己人手里可太冤了。她犹豫着,摸出袖中的匕首。却听得屋内一声哐当撞响。她焦心之下,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一刀甩飞下去,切断了银丝,门向内两侧敞开,芙蕖浑身都绷成了一根弓弦,一触即发,却什么危险也没等到。可是当她一抬眼,瞧见面前地板上,斜插着一把锋刃修长如禾苗的细刀时,眼睛却浮红了一片。谢慈是文臣。他出入不经常佩刀。但芙蕖认得他那把独一无二的凶器,刀柄下钳着一枚银打的莲花印。此刻他的刀尖三寸深深地没进了地下,而用刀身扛起了一截横梁,弯曲成了满弓的样子。那沉重的横梁下,一排细密的针钩,若是让它冲到身上,即便不死也得当场撕一层皮。芙蕖一脚踢开那老旧的木梁,刀身如蝉翼般弹出虚影,她用力拔出刀,上前几步,见到那尊菩萨像旁边,正委顿靠坐的身影。他侧头注视着她,那双淡漠的眼睛里什么感情也没有。庙里冲鼻的异香已经完全掩盖不住了。芙蕖闭上眼睛排出心中杂念,对他说:“我谢慈盯着她看了很久。芙蕖以为他会说点什么,但他一声也没吭,缓缓的垂下头,呕出了一口血。人紧接着就沉下了气息。芙蕖扔了刀就蹲下身扳他的脸。她这是活活把人给气晕了?谢慈的汗一层一层浸透了衣裳,但芙蕖摸他的身体却是冰凉。她并不知道,谢慈的内脏正如油煎火燎一般难受。她想到了苏慎浓曾经提过的南华寺往事。苏慎浓说撞见了他不知缘由的痛苦。想必正好是他凤髓发作的时候。芙蕖将揽过他的头,让他在怀里枕得更舒服一些。他利落分明的下颌线和致命的咽喉所在,皆毫无防备地露在她的眼下。不消片刻,她感觉到自己的体内的血脉也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躁动。芙蕖养了母蛊在自己的身体里,但却不知具体解毒之法。她垂眸望着谢慈干裂的嘴唇,忍不住用手碰了碰。当指腹离开那片柔软的时候,谢慈昏蒙中做了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将唇抿进了嘴里。芙蕖脑子里轰的一下,捏紧了他的衣袍。当一个人窥见自己的未来将以一种什么方式去死。所有的爱恨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但偶尔,死水也能溅起涟漪,人一旦活泛起来,也会在绝望中张开手,尝试着抓住点什么。芙蕖对他肖想多年,有七八成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张脸。江南江北走过了个遍,芙蕖再没见过比他更出尘的姿容。可惜,终究要成为别人的。莫名升出些英雄气短的悲戚。芙蕖再一次心想,若是她有命活,说什么也要为自己挣一挣,不图他的权,不图他的钱,单只为了这个人——她也想把他养在掌心里占有,尝尝金屋藏娇到底什么滋味。正当芙蕖心里兀自开花的时候。门外由远而近轰隆的马蹄声又撵上来了。但是方向与之前的追兵不同,恐是另一群人。芙蕖霎时间握紧了刀,环顾四周,庙里四面漏风,实在无处可藏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