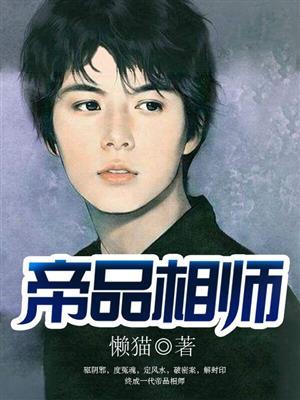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indigowhite个人资料 > 第37页(第1页)
第37页(第1页)
宫河见反驳不过,急赤白脸道:“你懂个屁!”
“吃串儿。”蒲龄听着吵,给他拿了一串肉。
“谢谢蒲龄哥!”宫河笑了,拿起肉就啃。
“这怎么桌上都没点儿酒啊,”孙绍南大嗓门说着,“哥们儿为你浴血奋战一晚上,连个酒都没有?”
“来一扎。”宫野懒洋洋地抬了一下手。
“白的!”孙绍南说。
“得,”闫润同情地拍了拍蒲龄的肩膀,“你今晚辛苦了。”
蒲龄刚想开口问为什么,宫野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看着闫润道:“说什么呢,我又不喝。”
不喝不喝,最后宫野还是喝了。
还喝了两瓶,脸都喝红了,看着比平时要健康不少。
平时脸就跟一吸血鬼似的苍白,现在好像更顺眼一点儿。
蒲龄盯着宫野想。
一帮人除了他和闫润都喝大了,孙绍南非拽着服务员小姐要给她来一首什么兄弟抱一下,吓得人放下烧烤就往外跑。
“蒲龄蒲龄,那什么,”闫润把周洋孙绍南还有宫河一股脑全塞进出租车后座,转头道,“你送一下衍哥,反正你俩住一块儿。”
“他呢?”蒲龄指着倒周洋身上还在手舞足蹈的宫河。
“还能让你一小孩儿送俩吗,住我家了。”闫润笑笑说。
“哦。”蒲龄点了下头。
闫润一帮人走了以后,蒲龄没管宫野,任他像一滩烂泥似的趴在桌上睡得昏天黑地。
桌上的花生还没吃完,蒲龄拿过来,一边剥一边吃。
等全吃完了他才拍干净手,起身去拉宫野。
送喝醉的宫野回家是个力气活,得吃饱了干。
蒲龄想着,抓着宫野的手臂,一手揽住了宫野的腰。
宫野的身体很热,没有想象中那么沉。
蒲龄叹口气,把他的手臂搭到自己的脖子后面。
宫野闷闷地嗯了一声,手指抓住了他的肩膀。
“。。。。。。”
蒲龄架着他,走出了烧烤棚,到外面去喊车。
出租车来得很快,蒲龄把宫野扔到后座上,想了五秒,也钻进了后座。
司机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儿,一路都在心情很不错地跟着学广播里一听就很不专业的的说唱。蒲龄被歌吵得脑袋疼,几次都没忍住要伸手关广播,又一想他好像没什么决定权利于是作罢。
宫野始终睡得很沉,眼睛闭着平平的,没打呼噜,呼吸也安静,胸口轻微有起伏。
他的头发好像又长了一点,像海藻一样乱糟糟地铺在肩膀上。
蒲龄坐在左边,看着宫野把脑袋贴在右边的窗户上,外面的路灯透进来,照着宫野的半边脸。
真是长了一张很好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