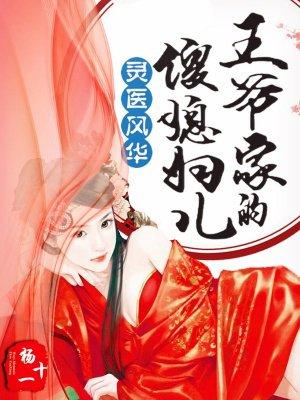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我什么向明月 > 第104章(第2页)
第104章(第2页)
吴寅用的不是巡检司人马,都是他自己从京中带来的亲卫。亲卫们黑衣蒙面,训练有素,和安十九的府兵迎面碰上,整装待战。
不远处的屋脊上,随着一声哨音破空射出,双方人马纷纷挥动兵戈,大喊着冲向对方。
雪越下越大,只子夜过半便积了厚厚一层,踩在松雪上清晰可闻嘎吱声响,瞧这鹅毛飞卷的趋势,隐有百年难得一见的苗头。
而在万人欢庆丰年的一夜,安庆窑后院第一次见了血,厮杀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此时的梁佩秋被一件浸着泠泠清香的外衣裹着,已策马穿过景德大街,直入西六所。
前朝多有战乱,为避祸保全老小,百姓们曾一度大肆开凿冰窖,及至今朝,太平盛世数十年,冰窖逐渐被弃用,转而盖起一座座窑房坯房,往日冰棱林立的场面再不复见。
徐忠原也有过封了冰窖的念头,被徐稚柳拦住了。
一方面西六所临靠镇郊,荒僻无人,不占用湖田窑的主要用地,封不封意义不大,另一方面随着新帝对青花瓷的喜爱越发狂热,事关名窑的争端也越发激烈,为留退路,徐稚柳不仅没封冰窖,还悄悄扩宽了冰窖,在下面挖出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
此事极为隐秘,就连徐忠也不知晓。
徐稚柳驾轻就熟地摸到暗门,随手扫过冰台,将外衫铺了上去,尔后放下人,他的动作是自己都不曾察觉的谨慎与温柔。
梁佩秋几要昏睡过去,冷不丁遭到一团寒气的刺激,神经一跳,人又清醒几分。她勉力睁眼,环视一圈后,视线定格在不远处正搓着手扫拾稻草的人身上。
他的外衫正垫在她身下,内里只一层薄薄的蓝色绸衣。时已入冬,即便绸衣絮棉,也抵不住寒窖的冰冷。
他一手搓揉稻草,将上面的冰碴子抖落,一手打着哆嗦在草堆里寻摸什么。不久,嚓声响起,冰窖亮起一簇光。
他点了火烛,回过头来,正对上她的视线。
梁佩秋唇色发白,声音很低:“周大人,我以为今夜你不会再出现了。”
徐稚柳将收整好的稻草抱起,用力甩了几下,可惜不是干稻草,多少有点湿冷,但也好过什么都没有,于是铺盖到她身上,薄凉的唇线里照旧是薄凉的话语,“还不到你死的时候。”
谁能想到安十九会用这一招?他以为顶多就是打一顿出出气,亦或关到牢里折磨一阵子,怎么都不会要了她的命,没想到……
其实安十九的试探已摆在明面上,用了春药还送了美姬,但凡她是个男子,什么事都不会有。即便有,只要她向安十九求饶,亦或随便找个男人,解了药就能活。
这不算什么要命的东西。
怪就怪在,周齐光也发现了这一点,却没将她交出去。
梁佩秋的手不由自主地摸向胸前。在和女姬的拉扯中,裹胸已经松散下来,随着呼吸,小小的山丘一起一伏。
她下意识攥紧衣衫,挡住胸前:“你是何时知晓的?”
周齐光动作一顿,和她目光相接,发现她的动作后意识到什么,往旁边退了一步。他看起来有几分闪避的意思,语焉不详道:“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你应该想,安十九发现了怎么办?”
“他已被我糊弄过去了。”
“是吗?”
这次回来,确实见她长进不少,都晓得男欢女爱那档子事了。徐稚柳道:“方才出来时,安十九的人马还在安庆窑。”
梁佩秋一怔,仔细回想先前的事。在被抱离小青苑时,她已是半昏迷的状态,似乎听到了响哨声,隐隐约约夹杂着兵器相击声。
安十九当真留了人马,黄雀在后?她一整晚没有看到白梨,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那些府兵动起手来,会不会伤害安庆窑的无辜奴仆。
这念头一起,到底放心不下,她挣扎着起身,想回去看看。谁知脚刚落地,双腿就是一软,整个人跌坐在地,就连攀着冰床借力都嫌吃紧。
尝试了几次后,她颓然跌坐回原位。
身体的热度明显好转,不似之前烧得她稀里糊涂,可药效明显还在,让她总觉身体某处空落落的,不住地想要索取什么。
这本是药物作用的生理反应,可对于未经人事的她来说未免过于羞耻,她强咬牙关,隐忍身体的浪潮,余光瞥向不远处的身影。
那人自被点破,就再也没有上前一步。
良久,还是徐稚柳先开了口:“安庆窑那头你不必担心,巡检司人马已赶了过去,还有吴寅亲自坐镇,安十九不会搞出什么不该有的人命官司。”
“谁知道他疯了能干出什么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