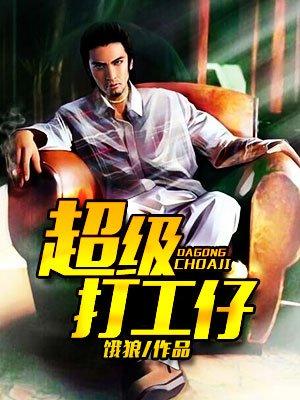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糊涂虫是骂人还是夸人 > 第7章(第2页)
第7章(第2页)
「赢了钱,谁还会住在那种又湿又闷的地方?」
井筒平四郎喝着麦茶皱起眉头,想起阿律憔悴的面孔。
「阿律就是为了这烦恼?」
「可怜哪!糟蹋了她那张标致的脸蛋。我也是一逮着权吉兄,就臭骂他一顿。」
「光挨骂是戒不了赌的。」
「要是阿朋还在就好了,权吉兄也不会这么荒唐。」
阿朋是权吉的亡妻,过世三年了,生前和阿德很要好。
「就算老婆在,也戒不了赌的。」
「不然,要怎么样才能戒呢?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平四郎瞄了小平次一眼。他想说的话,就写在小平次脸上:「没有」。
「你最好当赌博是种治不好的病。」
「那阿律可怎么办?总不能丢下她爹不管吧?那孩子真的是个孝女。」
平四郎捏着下巴想,就算是女儿,也没有道理一定不能丢下父亲吧?小时候曾经在门轨上又蹦又跳,巴望老天打坏父亲脑袋的这个人,本就认为所谓的孝心实在不怎么可信。世上被称为孝子孝女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是发自内心去孝顺长辈的?这一点平四郎相当怀疑。他认为绝大多数恐怕是阴错阳差,一度被冠上孝子孝女的名号,就摆脱不掉了。
但这话若不慎在阿德面前说溜嘴,后果不堪设想。一直以来,阿德服侍那对冥顽不灵的翁姑,细心看顾卧病不起的丈夫到送终,同时又辛动工作,没有半句怨言。至今,阿德仍然不明白,不是天底下的人都跟她一样。就拿平四郎自己来说吧,十年前父亲过世时,平四郎看着死者的脸,心想这老头收了那么多贿赂,只知道欺压弱小,最后不但寿终正寝,死前也没受什么苦楚,可见得世上根本没有神明‐‐若他把这些话老实告诉阿德,她必定惊惧交加,哭丧着脸直嚷着不敢置信会听到这种话吧?谁会这样想自己的父母?这不是真话吧?非逼得平四郎说「是啊,是骗人的」不可。
见平四郎不作声,阿德便站起来拌卤锅。
「要是管理人在就好了。」阿德发牢骚似地说。「他定会常规劝权吉兄,想办法要他别再赌。」
既然权吉眼睁睁看着阿律消瘦憔悴,仍沉迷赌博,那么就算久兵卫在,也拿他没辄吧。但平四郎没说出口,因为阿德一有满腹牢骚,便难以应付。
「说到管理人,我倒想起来……」阿德换了话题,「凑屋有没有来说新管理人的事情?」
「没有啊…」
阿德悄悄向四下张望一下,拿着汤杓,就往平四郎靠过来,压低声音说道:
「这阵子有些『胜元』的年轻人过来,收拾久兵卫爷的东西。」
「几时开始的?」
「就两、三天前。」
「今天也来了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去瞧瞧。」
平四郎站起身来。久兵卫住的三层楼房子,靠南紧邻前杂院。平四郎踱过去,反方向来了一辆大板车,正好就停在平四郎要去的那间屋子前。拉着大板车的年轻人,身上穿着「胜元」的短褂。
平四郎驻足观望,只见那年轻人卸下车上的行李、包袱,一一往屋里搬。东西不多,也不见家具。
「胜元」是凑屋开在明石町的料亭,久兵卫以前也在那里工作。平四郎拔着胡子想,看来是来了新的管理人了。这次也是「胜元」的人吗?
他还在一旁看,大板车上的东西已全数卸下,朝来时的方向去了。平四郎往久兵卫之前的住处靠近,小平次跟在他身后。
「一定是新来的管理人。」他也这么说。平四郎正要答话,正上方传来啪沙啪沙的扬翅声。他吃了一惊抬头望,乌鸦正展开黑色羽翼,从他们头顶飞过,然后翩然落在管理人家的屋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