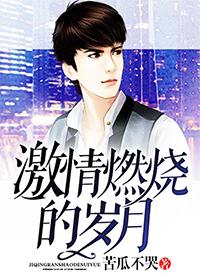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王冠cp恋爱大全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这所新剧场正在排演一处伦敦人民喜闻乐见的莎翁剧《哈姆雷特》,由于原本饰演哈姆雷特的男演员突然和人私奔去了美国,因此剧团才临时对外招募了新的男主角,也就是最近经济状况相当不妙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那天是下午场结束后的空隙,乔治娜从剧场的后门进入,隐隐地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传来,方向是剧场的后台。
推开一道半遮半掩的木板门之后,就看见环形的场地内大大小小聚集了附近街头许多的流浪儿和童工,其中有那么几个稍大的都伛偻着背,那是幼时被推入烟囱清扫、侥幸存活下来的残缺,而没有区别的是,每一个孩童的身影都是极单薄的,看不出颜色旧衣勉强裹住黑瘦的躯干,只一双双尚带稚气的眼在音乐的抚慰之下,流露出些许微弱的光芒。
只有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正在拉琴的歇洛克。
演奏充满激情,华丽的音符像一只只歌唱的夜莺,盘旋在这处空间中,令人倾倒。
有人黯然神伤,有人热泪盈眶,有人懵懵懂懂。
但没有人舍得打破此刻的静谧。
他身穿文艺复兴风格的戏服,以羊毛絮填充的达布里特,外罩衣长及臀的丝绒嘎翁,有些时日未曾修剪的黑色短发并没有抹上发油,自然地垂落着,因此显得他比往日里更加年轻,却也多了几分王子般的诗意忧郁。
光线从楼顶的天窗照射下来,仿佛一束无形的聚光灯,为这人高挑又清瘦的身形镀上了一层神性的光辉。
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闭着,眼窝处是两片深深的阴影,鼻梁挺直微勾,底下是两片抿得紧紧的薄唇,昭示着内心的不平静。
乐曲的曲调越发缠绵动人,酸涩的忧伤缠绕每个人的心头,但弓弦微动,极其精彩活泼的快板突然而至,把人们带到了热闹欢腾的氛围中,流利的快弓拨弦令人不禁想要随之起舞。
一曲终了,所有人脸上对于音乐的沉醉还没有消退,就连乐曲的演奏者,也沉浸在方才的余韵中。
直到一个留着遮住半边脸的长长刘海的黑发少年注意到了站在那儿的乔治娜,不禁惊呼道:&ldo;林恩先生!&rdo;
乔治娜是来向歇洛克告别的。
她即将坐明天一早的船从伦敦出发,途径多佛尔海峡,抵达布鲁塞尔,随后转陆路前往柏林。
&ldo;要去多久?&rdo;
&ldo;快则三月,慢则半年。&rdo;
&ldo;那么,衷心希望您的旅途将会愉快。&rdo;
&ldo;承你吉言。&rdo;乔治娜望着歇洛克眉间的一丝沉郁,不由地说:&ldo;也希望我回来之前,你能再次打起精神,福尔摩斯先生。&rdo;
歇洛克自嘲地笑了笑,答道:&ldo;不,只是对芝麻蒜皮的无聊委托,暂时觉得厌烦而已。&rdo;
他习惯性地去摸胸口内袋里的石楠根烟斗,然而忘记了身上穿的并不是自己的常服,而是哈姆雷特那身繁琐的戏服,因此只伸手摸了个空,不尴不尬地在胸口上掸了掸不存在的灰。
乔治娜点头,随手拿起桌上一份医学周刊翻了翻,问:&ldo;你在读这个?&rdo;
&ldo;是的,那上面有一篇关于遗传性凝血障碍的论文很有价值。&rdo;
&ldo;你是指德国人斯考雷恩提出的&lso;血友病&rso;这一概念么,福尔摩斯先生,我以为你或许会更关注另一篇关于血液凝固的环境研究。&rdo;
&ldo;事实上,我不太赞同后者的一部分观点。&rdo;歇洛克简短地说,似乎对于这个话题并没有继续下去的欲望,&ldo;我确信您本人对于这类杂志的兴趣不大,所以可能是您在最近去了皇家学会组织的内部沙龙,听到了一位您的朋友谈论此事。&rdo;
乔治娜没有直接承认,只说道:&ldo;更正一下,那一次的沙龙并不是皇家学会牵头的‐‐&rdo;
&ldo;而是大英发明制造公司。&rdo;歇洛克接口,忽然一笑,&ldo;我真后悔当初提出要去参观的是您的研究所,而不是现在这个公司,是我所做出的最不明智的选择。&rdo;
那一笑之后,这位先生脸上的表情又静止了下来,像是被一片阴云所笼罩,虽没有狂风暴雨,却有丝丝凉意沁入心头。
乔治娜从歇洛克的反应中猜测,那位名叫玛利亚瓦尔的女仆之死给他带来了不可言说的震动,而还未彻底浮出水面的莫里亚蒂教授也令咨询侦探首次窥到了伦敦地下世界的冰山一角,偏偏目前为止,别说抓人了,他甚至连对方的全名都没能得到。
这实在是有些令人挫败。
却也更加坚定了歇洛克找出幕后黑手的决心。
没有留下来欣赏今晚的演出,乔治娜随后就乘着马车离去了,因为她已经试探出咨询侦探暂时没有多余的精力追查那名神父被杀的后续,仍然沉湎于某种可以转化为动力的悲痛之中,想来莫里亚蒂教授隐藏在黑暗中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但即使找出这位咨询罪犯,苏格兰场又能以什么名义将他逮捕归案呢?
他既没有亲自动手,也大抵不会留下什么证据。
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的。
伦敦城里不仅潜藏着无数令人战栗的罪恶,也有着无法管束的灰色地带。
马车一路往东,由富人所居住的西区,进入了如同一幅黑白素描画般的东区,在确定没有可疑车辆跟随之后,在一条阴暗的巷子口稍微停了不到五秒,一个半大的少年就已经猫着腰蹿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