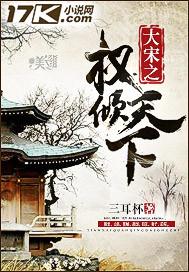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智相小卡1860内驾驶室 > 第十六章 两害相权取其轻(第1页)
第十六章 两害相权取其轻(第1页)
王侍郎听闻这话,又是一惊,原来这屋里还有一人。他身子微颤,想到自己星夜离开贡院,本来便是铤而走险,知道的人应当是越少越好。
不过,见到内屋出来之人,王侍郎一张嘴长得老大,显得意外万分。
“学生拜见侍郎大人。”柳明从内屋出来,礼貌行礼道。今夜,他原本念及自己的恩师生活清苦,便带些酒水猪头肉什么的,准备跟恩师好好唠唠。没想到半夜里又有访客。刚才躲在内屋,听闻堂堂礼部侍郎亲自为了自己的事情,不惜冒着风险赶来,顿时感动无比。
“侍郎大人为了学生,甘愿冒此风险,学生无以为报。”柳明下跪道。
王侍郎连忙扶起柳明,说道:“家事国事天下事。柳明,你的文章,我在贡院就看过,当时就料定你必进前三甲。此番前来与你恩师商谈,便是要商讨出个法子来。”
形势突变下,柳明能不能取得贡士之资,反而成了朝廷两党相争的激烈焦点。
柳明站在范仲淹身旁说道:“侍郎大人,其实这种时候,学生应该回避。毕竟,涉及到学生的省试名次。学生在这里大放厥词,实在是不好。”
王侍郎有些急了:“柳明,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要再客套了。你如果有什么良策,尽可以大胆地提出来……”
柳明躬身道:“那学生说两句。学生认为,此番还是先不宜过早地将矛盾公开化。虽然时间紧迫,我们还是需先探探宋尚书的口风。冤家宜解不宜结,我那日在金闺楼,因为误会绊倒了宋尚书,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为难我。如若这次不是他夫人出面干涉,我想宋尚书还是会把我的名字放在三甲之列。”
相比至于王侍郎的急躁,当事人柳明反而显得十分沉稳和冷静,似乎这谈论的不是事关他的名次。
王侍郎和范仲淹同时感到,柳明不过刚刚弱冠而已,却能在巨大的关键利益面前,保持沉稳,实在是有成为当朝宰辅的潜质和气量。
“恩。”范仲淹抚须道,一双洞穿世人之心的眼睛看着对方道:“柳明,你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当务之急……是得敲山震虎。”柳明的眼神熠熠闪光。
次日清晨,贡院早晨初雪融化,阳光淡淡在雪面上反着光。
贡院西房内,宋痒边咳嗽边穿着衣衫,这几天,他神色憔悴无比,夜中也是噩梦连连。
披上狼皮大氅,宋痒嗅着初晨清冷的空气,走到内堂用早点。然而,只吃了两口,便放下了筷子。
“大人……”厨子在一旁紧张地说道,“考虑到大人喜好清淡,这早饭,还是以往一碟酸咸菜,一碟皮蛋,还有一碟油炸花生。是不是不合大人胃口?”
宋痒摆了摆手:“老夫自己胃口有些差。没有你的事情。”
“大人主持春闱的确疲惫,还好,明日便是结束,大人可回家高枕无忧地休息了。”厨子奉承道。
宋痒站起身来,走到院中,衣衫飘飘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大人,大人。”一位门房跑了进来,禀报道,“门口停了辆马车,迟迟没有离去。”
“谁家的马车?”宋痒不耐烦道,“查清身份,告知他们这是贡院,必须尽早离开。”
门房禀报道,“好像是……范……范公家的马车。”
“范公?”宋痒诧异了,他神经突然紧张起来了,自己之前依稀听说,这柳明似乎拜范仲淹为师。宋痒心想,这个执拗的范老头,倒是难得又收了门徒。
但是,他怎么会突然要求见自己?
宋痒脑子转得飞快,自己黜落柳明的消息,应该是处于绝密状态。他根本不会想到,王侍郎已于昨夜冒着被送进刑狱的风险,跑到贡院外通风报信去了。
宋痒最近才得知,柳明为范仲淹新收的门生。大概是范仲淹为了自己的学生,想来疏通一下关系。
宋痒有些头痛,这范仲淹,在朝廷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即使在野,也是一动抖三抖。他要是与自己谈起这柳明的问题,宋痒估计自己肯定会被这个老头给搞得脑筋团团转。
“官家有令,贡院阅卷期间主考官不得见无关人员……”宋痒甩了甩衣袖,“你就跟范公说,宋某现在不便出迎,他日必将回访。”
那门官立即领命出去,没过一会儿又跑了回来。
“怎么了?没走?”宋痒血压都上来了。
“不是,大人。范公说他并无意违背圣旨,只是想送给大人一副字画。”门官禀报道,并呈上一副卷轴。
宋痒将卷轴慢慢展开,只见是夜色下的一户民宅内布景图,一张木床,两只木椅板凳。
宋痒心想这范仲淹,果然是老谋深算,一定是把要说的话,都藏在了画中。这样,即使自己将此画呈到皇帝面前,他也可以推脱得一干二净。
宋痒将画夹在腋下,漫步走入屋内,拿出画平铺在案前,盯着它直发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