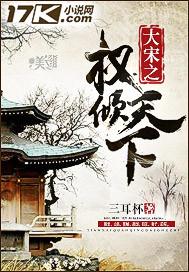下页小说站>智相电动轻卡 > 第十四章 不速之客(第1页)
第十四章 不速之客(第1页)
省试贡院门口的两条街前,都竖起了“回避”和“肃静”的令牌。虽然考试已经结束,但是门口守卫的兵丁不减反增,个个都是佩刀持枪,一脸警惕地盯着往来行人。
春闱后的阅卷日,仍然是异常重要的环节。
礼部尚书宋痒,以及一众礼部官员,都端坐在贡院内堂,个个神情紧张严肃。六千多份考卷,四千多万字的任务,全部压在这些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决不能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了事。
时辰一到,宋痒站起身来,高声道:“各位大人,省试乃是国家之抡才大典。官家曾亲自下诏给本官,诏曰:‘士子握椠怀铅,三年大比,一经屈抑,又须三年考试”,试官若“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本官接诏,诚惶诚恐,也望各位大人严格尽心阅卷。”
阅卷工作,十分辛苦。几位平均年龄年近六旬的考官,试卷不离眉与目,手巾频拭汗兼油污。一天下来,等到天色暗得需要点油灯时,已经是头昏眼花,灯光朱字两模糊。
这一天的劳顿,让几位上了年纪的考官,纷纷捶打着自己的肩膀和老腰,站起身来,算是勉强换一口气。
宋痒阅了一天卷,也是辛苦至极,他刚刚走到内堂门口,准备喘口气,就听得外面的兵丁跑进来汇报,“大人……有人在贡院门口,想要见您……”
宋痒脸色有些不悦,说道:“春闱阅卷期间,贡院外部全面封锁。为了阅卷公平,无论何人,一律不见。”
那兵丁听了之后,却仍然不走,似乎面有难色。
“怎么了?”宋痒问道,“还不走?”
那兵丁犹豫道:“大人,是大人的夫人要求见。”
“啊?”宋痒眉头一皱,心想估摸着那母老虎,又是想起什么事情,准备来教训自己。正好借着阅卷的由头,宋痒也不愿见他,说道,“锁院乃是宋律,无论是谁,都要一视同仁。”
那兵丁领了命令,到门房处没多久,宋痒在院内就听得外面一阵嘈杂之声。
两名门官捂着脸跑了进来,说道:“大人……夫人要硬闯进来,还带着公主。那公主殿下,一进门,不由分说,就一个巴掌打在小人脸上。小人实在是有些顶不住了。”
宋痒一听,沉默不语。自己老婆是皇亲国戚,权势滔天不说,还一天到晚跟着那个祁阳公主混在一起。那祁阳公主,从小受到宠溺,连官家都十分疼爱她,实在是刁蛮惯了。
两人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听到贡院内一声大吼:“宋痒,你这个老不死的,快给我出来!”
这吼声,真是平地一声惊雷响啊。那些守卫的兵丁们,见宋夫人和祁阳公主闯进来,全都面面相觑,更无人有胆敢出面阻拦。
“宋痒,你给我出来!”
宋夫人又是一声高喊。
那宋夫人经典的吼叫声越来越近,负责阅卷的礼部侍郎和员外郎们,见此情景,为了顾及宋痒的感受,纷纷找理由离开了。
宋痒叹了口气,搬了把椅子,坐在院中,只待那宋夫人和祁阳公主到来。
“宋痒,你个老不死的东西,终于在这里找到你了。”宋夫人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
宋痒站起身来,看着宋夫人,严厉道:“你个妇道人家,春闱阅卷日,跑到这里来大吵大闹,被御史知道了,还不参我一道?要是皇上怒了起来,把我这个礼部尚书革职,我看你这个尚书夫人还做得了吗?”
那宋夫人虽是母老虎,但是听到自己的相公可能因此受到波及,也一时愣住了,她语气软了些,说道,“我也不是想来闹事的……”
“呦,我看谁敢参我的姨夫?”一个娇嫩的女声响起。
宋痒见到那位站在宋夫人身后的年轻女孩,不得不下拜跪道:“微臣参见公主殿下。”
“姨夫,快请起。”祁阳公主笑道,“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你们聊着,我到旁边玩一会儿去。”说罢,便像轻风一样地跑了。
宋痒看到祁阳公主在贡院内乱窜,又想起上次她小时候玩火差点将东宫烧毁的劣迹,就感到血压上涌。连忙督促旁边的门官,万般叮嘱,让公主千万别进阅卷室内。
“好了,你别一口一个公主的了。”宋夫人冷笑道,“你要是真的能把公主,把我们郭家放在眼里,也不会做这么无耻的事情了。”
宋痒见夫人又要发作,立即将她带到偏房内,关上了大门。
“你快把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宋痒气得直颤抖。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宋夫人瞪着宋痒,“你说说看,上次你到金闺楼做了什么荒唐事?”
宋痒明白没有捉到证据,绝不能说,一口咬定道,“夫人,那一日老夫只是去会一个友人,没有别的想法。老夫为政十多年,讲得就是个身正……”
“身正?”宋夫人摇头叹气道,“看来,宋大人您没有关键证据,是绝对不会认的。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
见夫人又旧事重提,宋痒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宋痒!”宋夫人阴沉着脸道,“那个刘门房,都跟我说了……关于他怎么带你去的金闺楼,找的哪个姑娘,我都清楚!”
这一声,如同死刑判决书一般,让这位礼部尚书一时头晕目眩,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